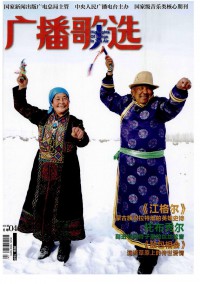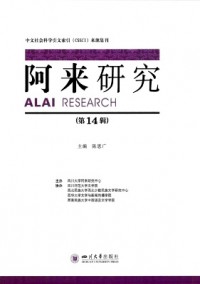藏族的文學(xué)藝術(shù)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藏族的文學(xué)藝術(shù)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fā)現(xiàn)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藏族的文學(xué)藝術(shù)范文第1篇
關(guān)鍵詞:民族文學(xué)藝術(shù)語言藝術(shù)表演藝術(shù)造型藝術(shù)
民族文學(xué)藝術(shù)起源于人類社會的勞動和多種社會需求,一個民族本質(zhì)上的特點(diǎn)充分蘊(yùn)含在文學(xué)藝術(shù)的內(nèi)容和形式之中,“每一個民族,不論其大小,都有它自己的,只屬于它而為其他民族所沒有的本質(zhì)上的特點(diǎn)、特殊性。”①所謂的民族性格是指一個民族在共同的文化背景和特定的社會文化歷史條件下,形成的對現(xiàn)實(shí)的穩(wěn)定的、共同的態(tài)度和習(xí)慣化的行為模式。我們平時(shí)所說的基本人格類型、民族性以及社會性格等概念,就是指民族性格。
民族文學(xué)藝術(shù)可分為語言藝術(shù)(指神話、童謠、故事、諺語、文學(xué)等)、表演藝術(shù)(主要指音樂、舞蹈)、造型藝術(shù)(指繪畫、雕塑、工藝美術(shù)、建筑、服飾等)和綜合藝術(shù)(指戲劇、電影)等幾大類型。每種藝術(shù)形式代代傳承和發(fā)展,都深深地烙上了民族的印記。
一、語言藝術(shù)
文學(xué)是一種語言藝術(shù),是社會生活在作家頭腦中的間接反映。一部優(yōu)秀的文學(xué)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一個時(shí)代、一個民族所特有的精神風(fēng)貌。
文學(xué)所具有的民族性格是受各民族語言、生活方式、精神信仰和神話傳說的影響,這些影響又具體體現(xiàn)在文學(xué)作品的內(nèi)容和形式等方面。以中國少數(shù)民族蒙古族文學(xué)為例。在蒙古族文學(xué)中,再現(xiàn)了“天蒼蒼,野茫茫,風(fēng)吹草低見牛羊”的草原自然景象,“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經(jīng)濟(jì)形態(tài),“毛氈帳裙”“食唯肉酪”的傳統(tǒng)生活方式,使蒙古族文學(xué)散發(fā)著清新濃郁的草原生活氣息和一種剛健雄渾之美。這種獨(dú)特的文學(xué)藝術(shù)風(fēng)格只能歸屬于特定的民族文化范疇,也只能在特定的民族生活土壤中萌生、發(fā)芽。反映了蒙古族獨(dú)特的民族性和社會性格。
文學(xué)作家在運(yùn)用形象思維進(jìn)行創(chuàng)作時(shí),總會把他所要塑造的人物性格注入民族精神,使整個文學(xué)作品滲透著本民族人民的共同心理素質(zhì)、共同審美習(xí)慣和共同的情感體驗(yàn)。如屠格涅夫的《父與子》,托爾斯泰的《復(fù)活》《安娜?卡列尼娜》,果戈理的《死魂靈》《欽差大人》等眾多作品,都成為膾炙人口的傳世佳作。眾多文學(xué)大師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大多個性鮮明,人們既能夠在作品中尋找到不同歷史時(shí)期的鮮明的人物性格,又能夠捕捉到該民族所具有的共同的民族性。
二、表演藝術(shù)
各民族的生態(tài)環(huán)境不同,歷史發(fā)展的軌跡也不同,因此不同種族、文化和背景下的不同群體會形成迥然各異的表演風(fēng)格,不同民族突顯出不同文化的藝術(shù)表現(xiàn)形式。
1.舞蹈
舞蹈是以人體為媒介的表演藝術(shù),它同歌唱一樣在人類社會的初期伴隨著人們的勞動和社會生活而產(chǎn)生。世界各民族的舞蹈是該民族歷史、文化的標(biāo)志之一,是民族風(fēng)俗和民族生活的描繪和積淀,反映著本民族的民族心理、審美情趣和民族性格等文化現(xiàn)象。
在舞蹈形式的表演藝術(shù)中,朝鮮族舞蹈獨(dú)具特色。鶴在朝鮮人民心目中是善良、純潔、長壽的象征,是圖騰崇拜的藝術(shù)形象。崇鶴心態(tài)經(jīng)過長期的藝術(shù)加工與不斷升華,形成舞蹈最基本的步態(tài),這種柔韌、飄逸的鶴步充分展示出舞者典雅、飄逸、瀟灑的風(fēng)格,創(chuàng)造出不同的舞蹈境界。另外,朝鮮歷史上曾多次遭受外來侵略,長期的反入侵斗爭和抗暴斗爭歷練了朝鮮族人民勤奮團(tuán)結(jié)、堅(jiān)韌不拔、自強(qiáng)不息的民族精神,反映在民間舞蹈中就形成了內(nèi)韌外柔、柔中蘊(yùn)藏著剛勁的民族性格。
塔吉克族是中國古老的高原民族,塔吉克人民世代生活在高原缺氧、風(fēng)雪嚴(yán)寒的艱苦條件下,因此塑造了他們淳樸樂觀、不畏艱辛的民族性格。正因?yàn)槿绱耍巳税漾椬鳛橛⑿鄣南笳鳎⑶野褜椀某缇春拖矏壑槿谌朊褡逦璧傅谋硌葜校何枵哒归_雙臂,像雄鷹般的勇猛矯健;身姿的起伏舒展、快速變化又表現(xiàn)了鷹起隼落的跳躍和扶搖直上的連續(xù)盤旋。塔吉克族舞蹈濃郁的民族風(fēng)格和藝術(shù)特色是受特定的生態(tài)環(huán)境、民俗生活和傳統(tǒng)文化的深刻影響,承載著民族文化的各種要素,印刻著民族所獨(dú)有的標(biāo)志,是民族認(rèn)同的語言符號。
2.音樂
音樂是在時(shí)間過程中展示的訴諸聽覺的一門表演藝術(shù),它的基本手段是用有組織的樂音構(gòu)成有特定精神內(nèi)涵的音響結(jié)構(gòu)形式。音樂中體現(xiàn)的豐富情感反映了各個民族的勞動生活、審美情趣和民族性格,成為表現(xiàn)民族心理的特定符號。
肖邦的瑪祖卡舞曲素材主要是以民間瑪祖爾舞曲為基礎(chǔ)的,表現(xiàn)了“人民的靈魂”。瑪祖爾舞的音樂節(jié)奏通常是強(qiáng)烈多變的重音,它可以落在小節(jié)的任何一拍、兩拍甚至有時(shí)落在小節(jié)的所有三拍上,最常見的是重音在第二拍。這些好像“頓腳”一般的強(qiáng)烈重音,活現(xiàn)出斯拉夫民族特有的民間舞蹈風(fēng)格,形成鮮明的音樂氣派和風(fēng)格。
19世紀(jì)30年代至20世紀(jì)初葉,俄羅斯出現(xiàn)了一批發(fā)展本民族音樂的作曲家——“強(qiáng)力五人組”。在音樂上除了繼承和借鑒西歐古典和浪漫主義音樂的風(fēng)格傳統(tǒng)外,主要強(qiáng)調(diào)在自己的創(chuàng)作中采用民族的題材和民族形式,描寫民族的風(fēng)土人情和民間神話傳說,體現(xiàn)自己民族的審美心理、美好夙愿和民族性格等。正是有了這樣一批民族音樂家,才使俄羅斯民族音樂由自立走向世界,確立了俄羅斯民族音樂在世界樂壇不可撼動的地位,成為人類共同的、世界性的民族藝術(shù)。
三、造型藝術(shù)
造型藝術(shù)又稱美術(shù),指用一定的物質(zhì)材料塑造可視的平面或立體感性形式的藝術(shù),故又稱為“視覺藝術(shù)”或“空間藝術(shù)”,包括繪畫、攝影、雕塑、建筑、工藝美術(shù)、服飾等。造型藝術(shù)帶有顯著的民族性格,集中反映了本民族對美的追求,在其作品中無不印著本民族精神的烙印。
1.繪畫、雕刻
繪畫、雕刻藝術(shù)在再現(xiàn)民族特有的生命形式時(shí)表現(xiàn)力尤為突出,傳遞了民族特定的文化背景、生產(chǎn)生活方式以及生理心理諸多內(nèi)外因素交互作用的民族審美情感,昭示著生命之光、民族之魂。
狩獵游牧民族用極具民族風(fēng)采的繪畫語言來表現(xiàn)民族獨(dú)有的情。素有“世界屋脊上的民族”之稱的藏族,其繪畫追求流動卷曲的紋樣,渾厚樸拙的造型,強(qiáng)烈對比的色彩,奔放剛勁的線條,充分顯示出人對生命之渴望和對大自然的膜拜心理,強(qiáng)化著民族審美情感。另外,蒙古族用動態(tài)美的審美心理來刻畫造型,(轉(zhuǎn)第133頁)(接第141頁)捕捉大自然中奔騰跳躍、雄偉健美的生命瞬間;用放縱粗獷的筆觸,凝重簡練的線條,厚實(shí)雄渾的墨色來潑寫民族精神和抒發(fā)真摯情感。
新西蘭的毛利雕刻文化是毛利民族文化精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毛利雕刻記載了每個部落優(yōu)美的故事和對祖先神靈的崇拜,滲透了毛利不同時(shí)期的社會特征與鮮明的民族性格。毛利的木雕、骨雕與玉雕構(gòu)思奇特、細(xì)膩而又粗獷,具有強(qiáng)烈的民族氣息與濃郁的古老毛利民族的文化特征。
2.工藝、服飾
工藝、服飾等藝術(shù),同樣體現(xiàn)著大量的民族文化信息、價(jià)值觀、智慧和情趣。以服飾為例,各個民族的服飾文化都具有自己鮮明的,能夠反映本民族歷史、文化特點(diǎn)的個性特征。這種特征表現(xiàn)在款式、原料,也表現(xiàn)在工藝、色彩、刺繡圖案等諸多方面。
屬于漁獵采集經(jīng)濟(jì)文化類型區(qū)的鄂倫春、鄂溫克、赫哲族,其服飾上留下了高寒地帶和原始森林地理環(huán)境的濃厚印痕。為了適應(yīng)寒冷的狩獵生活,鄂倫春、鄂溫克人一年四季都要穿袍服,他們厚重的袍服都要用狍皮、旱皮、鹿皮等制成,呈現(xiàn)出古樸、粗獷、稚拙的美。赫哲人的魚皮服同樣說明了這一點(diǎn)。他們沿江而居,其賴以生存的物質(zhì)資源,也在赫哲族的服飾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赫哲族早年穿的衣服從頭到腳都用魚皮為原料,如魚皮帽、魚皮衣褲、魚皮套褲、手套、子及魚皮等。新晨
而草原畜牧類型民族的服飾,形成了特殊民族風(fēng)格。草原大漠和延綿起伏的高山為草原民族提供了縱橫馳騁的廣闊場所,培養(yǎng)了他們的粗獷豪邁的個性,尤其在服飾方面體現(xiàn)出色彩艷麗、紋樣線條分明的風(fēng)格。如蒙古族、藏族服飾原料主要源于牲畜的皮毛。為了御寒,服裝大多以樣式寬大、厚重為主,尤其是藏族大部分地區(qū)都穿以水獺皮、豹皮、虎皮為邊,錦緞為面的羊皮袍,頭戴金花帽、狐貍帽、紅纓穗白氈帽等。可見,服飾藝術(shù)是民族在特定環(huán)境背景下的產(chǎn)物,更是民族心理、民族性格的外化表現(xiàn)形式。
結(jié)語
一個民族憑借什么可以被國際尊重,讓世界認(rèn)同?只有民族的本土文化才是對世界文化和人類文明的獨(dú)特貢獻(xiàn),才能不為其他民族所取代。“一方水土養(yǎng)一方人。”文學(xué)藝術(shù)所具有的民族性格,不僅塑造了一個民族社會成員所獨(dú)有的認(rèn)知能力、審美心理、民族性和智力能力,強(qiáng)化了民族意識和民族認(rèn)同感,更保持了世界民族文化的多樣性。
注釋:
①斯大林.與民族、殖民地問題.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77頁.
參考文獻(xiàn):
[1]王軍,董艷主編.民族文化傳承與教育.中央民族大學(xué)出版社,2007年版.
[2]王宏建.藝術(shù)概論.文化藝術(shù)出版社,2005年版.第125頁.
[3]方鐵,何星亮主編.民族文化與全球化.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
[4]陳自明著.世界民族音樂地圖.人民音樂出版社,2007年版.
[5]梁一儒,宮承波著.民族審美心理學(xué).中央民族大學(xué)出版社、內(nèi)蒙古大學(xué)出版社,2004年版.
藏族的文學(xué)藝術(shù)范文第2篇
關(guān)鍵詞:藏族民歌;演唱技巧;演唱風(fēng)格;“造型”
一、演唱技巧的“造型”
對于音樂專業(yè)的學(xué)生來說,并非每個人都具備高亢嘹亮的嗓音條件及生活閱歷,在演繹作品時(shí),就要通過聲樂技術(shù)把握聲音的“造型”。如:《安塔拉伊》這首作品的聲音“造型”就需要我們通過流暢的聲音、深且流動的氣息、高的聲音位置等技巧性問題進(jìn)行強(qiáng)化訓(xùn)練。
(一)聲部的確立:這首作品是一首女聲獨(dú)唱歌曲,一般由抒情女高音演繹比較合適,因?yàn)檫@種聲音音域一般在(C1-C3),其音色輕柔,聲音甜美有舒展性,而《安塔拉伊》這首歌曲的音域在C1-C3之間,歌曲風(fēng)格比較深情、委婉、旋律比較悠揚(yáng)、伸縮性強(qiáng),所以從音色、情感、歌曲的特點(diǎn)上來說更符合。
(二)音準(zhǔn):這首歌曲是升f小調(diào),中間并沒有變換調(diào)性,但是在歌曲中多次出現(xiàn)臨時(shí)變化音(如:#d #a #c 等),體現(xiàn)出作品細(xì)膩的情感表達(dá)。
(三)節(jié)奏型:全曲節(jié)奏比較穩(wěn)定、舒緩,約每分鐘52拍。作品中的節(jié)奏型基本都是由二八、前八后十六、四十六、前十六后八、二分音符、切分節(jié)奏等這些基本節(jié)奏型構(gòu)成,使作品的律動性增強(qiáng)。
(四)大跳:在這首歌曲中多次出現(xiàn)純四度、純五度(如:歌曲一開始 #4-7,后面出現(xiàn)3-7、#1-#4等)的大跳音程,這也是藏族歌曲中非常普遍的特點(diǎn),在演唱大跳音程時(shí),就要求我們演唱者必須把握好氣息的支撐、聲音的連貫、聲音支點(diǎn)支配自如以及喉頭的穩(wěn)定等技術(shù)性的問題,只有充分運(yùn)用掌握這些發(fā)聲技巧,才能把這些大跳的音程演繹好。
二、演唱風(fēng)格的“造型”
(一)作品的了解:該作品是一首藏族歌曲,是著名藏族史詩《格薩爾王傳》的插曲,作品源自地處海拔較高的雪域高原,具有非常獨(dú)特的地域性,風(fēng)格特點(diǎn)歌詞在兩句體的基礎(chǔ)上運(yùn)用重復(fù)等手段,發(fā)展到了四句體,歌詞含義簡單、明了,讀之如行云流水,起止自然,表達(dá)了男女的愛戀之情,曲調(diào)悠揚(yáng)、細(xì)膩、委婉。
(三)作品的情緒定位:有了好的演唱技巧,沒有感情,那樣的歌曲很空洞,就像一個人有了身體沒有靈魂一樣,歌曲的演唱情感就是整首歌曲的靈魂。《安塔拉伊》是一首情歌,在演唱過程中,首先要具備情歌所共有的特點(diǎn),如:深情、細(xì)膩、悠揚(yáng)等,同時(shí)要挖掘藏族情歌獨(dú)有的特點(diǎn)。如歌曲一開始兩句“啊……”這個旋律,都需要用大呼吸來演唱,要想象在雪域高原上大聲呼喊,聲音由近及遠(yuǎn),的感覺,同時(shí)感覺回聲不斷。第二句聲音要更加的釋放,從而引出后面歌詞部分:“安塔拉伊,山不在高低,只要草兒青青,草兒青青,安塔拉伊。”歌詞用訴說的形式,用小呼吸演唱,從音樂情感的表達(dá)上,應(yīng)該細(xì)膩、委婉。較引子部分情緒稍微平淡點(diǎn),與之前形成比較。第二段“安塔拉伊,泉不在大小,只要水兒清凈水兒清凈,安塔拉伊”感情較之第一段要更深情,唱出層次感。前面兩段是借“山不在高低,只要草兒青青。泉不在大小,只要水兒清凈”運(yùn)用比喻的手法,委婉的表達(dá)自己的心意。而后兩句的“啊……”的演唱要更加悠揚(yáng)、深情,將感情進(jìn)行一個過度,使旋律拉開、釋放,引出后面全曲的部分,表達(dá)主題思想:“戀人啊,不再窮富,只要有顆真誠的心,真誠的心,安塔拉伊。”演唱到這里,情感要得到一個爆發(fā),更加的深情、激動。最后:“唔……”是全曲結(jié)尾部分,用哼鳴的方法演唱,悠揚(yáng)點(diǎn),唱向遠(yuǎn)方,非常自然的結(jié)束全曲。
三、結(jié)語
藏族民歌《安塔拉伊》是藏族情歌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首,曲調(diào)細(xì)膩悠揚(yáng),朗朗上口,歌中運(yùn)用的比喻貼切、惟妙惟肖、形象生動,歌詞含蓄蘊(yùn)藉、思想內(nèi)容深邃而豐富,歌中所具有的人民性、廣泛性和高度的思想性,又正是使歌曲的藝術(shù)性不斷完美的重要因素,是民間文學(xué)藝術(shù)中瑰麗的花。
參考文獻(xiàn):
[1]杜亞雄.中國少數(shù)民族音樂[M].中國文聯(lián)出版社,1986.
[2]覺嘎.傳統(tǒng)音樂的結(jié)構(gòu)形態(tài)研究[M],上海音樂學(xué)院出版社,2009.
[3]更堆培杰.音樂史略[M],人民出版社,2003.
[4]王宏濤.《論聲樂表演藝術(shù)中的情感體》[M],陜西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04.
[5]周曉音.《聲情并茂的審美思考》[J],音樂學(xué)探索,2002.
[6]趙梅伯.歌唱的藝術(shù)[M],上海音樂出版社,1997.
[7]沈湘.李晉瑋等整理﹒沈湘聲樂教學(xué)藝術(shù)[M],上海音樂出版社,2008.
[8]嘉雍群培. 雪域樂學(xué)新論,中央民族大學(xué)出版社, 2007.
[9]施詠.中國民族音樂,安徽文藝出版社,2008.
藏族的文學(xué)藝術(shù)范文第3篇
[關(guān)鍵詞]新世紀(jì);藏區(qū)藏族文學(xué);現(xiàn)代視域;文化沖突;多民族書寫
中圖分類號:I059 文獻(xiàn)標(biāo)識碼:A 文章編號:1674-9391(2016)01-0036-06
二十一世紀(jì)初,中國市場經(jīng)濟(jì)乘著改革開放的強(qiáng)勁之風(fēng)向縱深發(fā)展,黨和國家開發(fā)西部,建設(shè)西部的戰(zhàn)略部署帶動了西部邊遠(yuǎn)地區(qū)經(jīng)濟(jì)建設(shè)的活躍和興盛。在此背景下,地處西部的藏區(qū)的社會文化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藏區(qū)社會受經(jīng)濟(jì)建設(shè)的活躍,交通、通訊的發(fā)展,旅游市場的開發(fā),教育事業(yè)和科技文明的普及與進(jìn)步,以及媒介引導(dǎo)和信息影響等多種因素的強(qiáng)勢介入,不僅民眾生活面貌有極大改變,精神視域也急速打開,藏區(qū)社會發(fā)生著迅猛深刻的文化轉(zhuǎn)型。在文化轉(zhuǎn)型的過程中,伴隨藏區(qū)社會現(xiàn)代化意識的日益深入,藏區(qū)文化結(jié)構(gòu)中呈現(xiàn)出多元復(fù)雜的文化因子,而文化因子間也持續(xù)地發(fā)生著各種碰撞、搏擊。這種情況反映在文學(xué)創(chuàng)作中,必將構(gòu)成繁復(fù)多棱的文學(xué)鏡像――藏區(qū)個人主體意識形成與個性心理結(jié)構(gòu)改變,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糾結(jié)交融,現(xiàn)實(shí)與信仰若即若離,文化沖突的疊現(xiàn)、文化精神的式微,引發(fā)藏區(qū)藏族作家以“他者”的眼光重新審視自我,審視現(xiàn)實(shí)。如果說從二十世紀(jì)五、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中期,以饒介巴桑、伊丹才讓、降邊加錯、益西丹增等為代表的藏族作家傾心地創(chuàng)作以政治抒情、政治敘事為主題的作品,以表達(dá)藏族同胞翻身解放的喜悅,對帶領(lǐng)他們翻身求解放者的贊美感激,對現(xiàn)實(shí)的歌唱和對未來的希翼;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到二十世紀(jì)末,以扎西達(dá)娃、阿來、班覺、索朗仁稱、蒼林、央珍、梅卓等為代表的藏族作家在文化尋根和思想開放的文化熱流下,注目于民族文化的發(fā)掘?qū)ひ挘髨D在文化堅(jiān)守中,把握住民族精神之根。文化敘事、文化書寫成為他們創(chuàng)作的主要目標(biāo)。然而,新世紀(jì)藏區(qū)文化轉(zhuǎn)型的巨大變化,不僅催生了一批更富現(xiàn)代眼光和現(xiàn)代思維的藏區(qū)藏族新生代作家,也讓在二十世紀(jì)八、九十年代走向成熟和成功的藏區(qū)藏族作家們刷新了創(chuàng)作視界,豐富了文學(xué)積累,增添了書寫藏區(qū)多元世界,擴(kuò)大創(chuàng)作視野的自信和能力,他們跳出政治敘事和文化敘事的創(chuàng)作舊路,探尋、開辟一種更富現(xiàn)代性和人類性的多元書寫與文化共生的文學(xué)發(fā)展新路。在藏區(qū)藏族新老作家共同努力下,藏區(qū)藏族文學(xué)自將迎來文學(xué)書寫的新局面。那么在新世紀(jì)藏區(qū)藏族文學(xué)創(chuàng)作中,與之前相比在現(xiàn)代多元文化影響下藏區(qū)藏族文學(xué)創(chuàng)作獲得了怎樣的進(jìn)步?這是本文所要論述的問題。綜觀新世紀(jì)藏區(qū)藏族作家的創(chuàng)作,總體上呈現(xiàn)著新的狀貌――在現(xiàn)代視域里關(guān)注并反映藏區(qū)文化變遷中的文化沖突,展示多民族文學(xué)書寫的積極姿態(tài),呈現(xiàn)出藏區(qū)藏族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新維度。本文將從以下三方面給予闡述。
一、現(xiàn)代視域下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建構(gòu)
文化進(jìn)步往往先從文化中心向文化邊緣地帶推進(jìn)。二十世紀(jì)八、九十年代,中國的改革開放使其社會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以內(nèi)地城市為核心的文化中心,實(shí)現(xiàn)了社會文化的成功轉(zhuǎn)型。那么當(dāng)文化變遷推進(jìn)到邊緣文化地帶時(shí),走進(jìn)新世紀(jì)的藏區(qū)社會就迎來了文化轉(zhuǎn)型的現(xiàn)實(shí):社會生活模式改變;技術(shù)文明與商業(yè)經(jīng)濟(jì)活躍;交通和傳媒發(fā)達(dá);生活視界擴(kuò)展;現(xiàn)代文明深入;個人主體意識覺悟;個性心理結(jié)構(gòu)改變以及隨之而來的族群傳統(tǒng)式微和危機(jī)等等,這些改變正是新世紀(jì)藏區(qū)社會文化轉(zhuǎn)型的標(biāo)識。文化變遷帶來新世紀(jì)藏區(qū)藏族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新視野。在文化變遷中,一方面是藏區(qū)藏民生活形態(tài)與思想意識的變遷,給創(chuàng)作群體提供了清晰的文化鏡像,提供了思考路徑和寫作資源;另一方面是現(xiàn)代文化意識為作家們燭照現(xiàn)代點(diǎn)燃了理性思想的燈盞。藏區(qū)藏族作家們的創(chuàng)作思維在應(yīng)對文化轉(zhuǎn)型和反映這種文化變遷的創(chuàng)作中表現(xiàn)出積極的現(xiàn)代建構(gòu)姿態(tài)。順應(yīng)文化變遷的勢頭,關(guān)注藏區(qū)藏族社會生活,審視民族傳統(tǒng),讓作家們選擇了面向當(dāng)下,走向現(xiàn)代的寫作立場。因而新世紀(jì)藏區(qū)藏族文學(xué)創(chuàng)作集體性地反映出顯明的現(xiàn)代視野。
其首先表現(xiàn)為一種進(jìn)步開放的創(chuàng)作意識和富于人類意識的書寫情懷。在阿來、達(dá)真、萬瑪才旦、龍仁青、澤仁羅布(尹向東)、尼瑪潘多、次仁羅布、江洋才讓、白馬娜珍、多吉卓嘎、才旦、格絨追美等等藏區(qū)藏族作家的創(chuàng)作中,他們超越了20世紀(jì)50-80年代的政治敘事和80-90年代的文化敘事,轉(zhuǎn)入一種復(fù)調(diào)式的多元文化與多民族敘事的共聲書寫。阿來的《格薩爾王》不僅僅是對民族史詩的重述,更是以現(xiàn)代眼光對民族原型品質(zhì)作更富于人類意識的重釋。在敘述格薩爾王的史跡時(shí),既寫英雄除妖降魔的偉績,也寫他濫殺無辜的暴行,于是解構(gòu)了對民族傳統(tǒng)之神的迷信,揭示了普遍性的人性弱點(diǎn),民族自省意識昭昭于文。在《瞻對》中,他以現(xiàn)代批評家的姿態(tài)主動介入民族歷史的反省:在敘述民族地域的歷史中反映民族本位與“他者”民族交融的艱難跋涉;從民族“夾壩”精神透視民族性格心理的弱點(diǎn);從國家權(quán)力對藏地族群的治理,探索多民族交融同一的可能性;并以現(xiàn)代眼光審視瞻對藏民在歷史文化悖論的渦漩中沉溺久遠(yuǎn),難融現(xiàn)代文明的生存困境。于是“族性”、“民族”、“國家”這些概念獲得了新世紀(jì)人類學(xué)理論中“將其置于建立在這些屬性基礎(chǔ)上的共同體觀念(ider)中加以詳盡闡釋” [1](P.4)的可能性。阿來這種進(jìn)步的歷史觀無疑體現(xiàn)著一個有現(xiàn)代識見和理性思想的作家對人類生存困境的關(guān)懷思考。江洋才讓的《康巴方式》在人與自然、文明與野蠻、族群與國家的多重主題意蘊(yùn)中傳達(dá)厚重的人類悲憫情懷,展示闊大的多民族國家想象。龍仁青的《失落的家園》、《光榮的草原》、何延華的《立春》、阿來的《空山》、《大地的階梯》、澤仁羅布的《騎在馬上》、《河流的方向》、達(dá)真的《康巴》、《命定》等等作品都迸射著現(xiàn)性的思想火花。
其次,這種現(xiàn)代視域還表現(xiàn)為作家們創(chuàng)作中借鑒現(xiàn)代藝術(shù)眼光,實(shí)現(xiàn)對民族藝術(shù)傳統(tǒng)的超越和更新,從而使藏區(qū)藏族文學(xué)煥發(fā)出新的美學(xué)光彩,獲得更具世界性品格的藝術(shù)表達(dá)的可能。在他們的創(chuàng)作中能看到藏族作家們“是怎樣從自己的文化出發(fā)開辟了漢語言文學(xué)新的語感,新的想象空間,并找到了一些什么樣的表達(dá)這些想象的更自如、更詩意,當(dāng)然也是更為文學(xué)化的方法。” [2](P.206)他們借鑒并突破藏族傳統(tǒng)文學(xué)“萬物有靈”、“人神同構(gòu)”的想象空間和單線敘事模式,將民族神性思維方法和歷史傳奇敘事或圓形敘事模式與現(xiàn)代寓言、散點(diǎn)透視、意識流、內(nèi)心獨(dú)白、回憶閃念、夢境書寫、聯(lián)想、幻象、隱喻、象征等等現(xiàn)代藝術(shù)形式和藝術(shù)手法結(jié)合,構(gòu)成新的魔幻現(xiàn)實(shí)或非虛構(gòu)傳奇以及多重奏結(jié)構(gòu)形態(tài),營造出神秘莫測,如真似幻,變化多端的文學(xué)藝術(shù)境界,傳達(dá)出鮮活而靈動的藝術(shù)美感。覺乃?云才讓《披著袈裟的牛角》用夢境構(gòu)造了一個奇幻鮮活的現(xiàn)實(shí)世界,現(xiàn)實(shí)人類的“陌生感”、孤獨(dú)感躍然紙上;阿來的《夢魘》借荒誕不經(jīng)的夢境寫光怪陸離的城市文化形態(tài)下城市人的生存狀態(tài),隱喻和嘲諷直抵人類靈魂深處。次仁羅布的《殺手》、《傳說》、才旦的《一對夫妻在陰世和陽世關(guān)于一個城市的對話》、《陰陽之界》、龍仁青《一雙泥靴子的婚禮》、澤仁羅布《魚的聲音》、尼瑪潘多的《紫青稞》等嫻熟運(yùn)用各種現(xiàn)代主義文學(xué)手法,在突破民族文學(xué)傳統(tǒng)思維基礎(chǔ)上不斷花樣翻新,都表現(xiàn)出對民族文學(xué)藝術(shù)傳統(tǒng)的超越和創(chuàng)新,因而莫不意味著他們與世界文學(xué)的接軌而具有先鋒性的品質(zhì)和意義。其創(chuàng)作獲得了現(xiàn)代意義的審美價(jià)值。
總體而言,新世紀(jì)藏區(qū)文化轉(zhuǎn)型,民眾生活行為與精神意識等文化基質(zhì)的現(xiàn)代性開拓與構(gòu)建,為藏區(qū)藏族作家們的創(chuàng)作提供了現(xiàn)實(shí)文化形態(tài)的參照物,也推動作家們建立起現(xiàn)代性的創(chuàng)作思維和文化審視的眼光。在這種獨(dú)特而進(jìn)步的思維和眼光下,關(guān)注文化變遷潮汐,以現(xiàn)性意識面對文化沖突的起落伏藏,成為藏區(qū)作家創(chuàng)作中的一個重要維度。
二、文學(xué)書寫中文化沖突的現(xiàn)代審視
文化沖突是一個社會、一個文化區(qū)域在文化變遷和文明發(fā)展過程中必定要經(jīng)歷的陣痛。同時(shí)“文化沖突是文化發(fā)展的重要動力”。[3](P.299)人類文化學(xué)家將文化沖突分為區(qū)域性、時(shí)代性、民族性、階級或政黨性以及集團(tuán)性五種。在現(xiàn)代中華民族整體文化結(jié)構(gòu)中,新世紀(jì)藏區(qū)文化沖突主要表現(xiàn)為前兩種――區(qū)域性與時(shí)代性。區(qū)域性文化沖突指外地與藏區(qū)本土文化間的沖突,如城鄉(xiāng)文化沖突,農(nóng)牧與商業(yè)文化沖突,開放的中心地域與封閉的邊緣地域間的文化沖突。時(shí)代性文化沖突指現(xiàn)代與傳統(tǒng)、新與舊間的文化沖突,如思想觀念的沖突、生活模式的沖突等等。在新世紀(jì)藏區(qū)藏族作家創(chuàng)作中,涉及的文化沖突的內(nèi)涵表現(xiàn)大多集中于藏區(qū)倫理意識、生活觀念、生活方式等文化結(jié)構(gòu)形式的保守與轉(zhuǎn)型間的沖突。作家筆下的文化沖突表現(xiàn)得相當(dāng)豐富真實(shí)。有舊家庭形式的漸變和解體,新舊婚戀觀的博弈和建立:如多吉卓嘎的《藏婚》寫一妻多夫藏族家庭,在現(xiàn)代文化潮中男女主人公從個體意識的覺醒到新型婚戀觀的建立所產(chǎn)生的文化沖突。沖突的結(jié)果是男女主人公各自掙脫了傳統(tǒng)的羈絆,而獲得愛情的新生;有生活觀念和生活方式的轉(zhuǎn)型沖突。次仁羅布的《前方有人等她》寫藏族夏嘎老太的兒子在城市生活中沉迷變異,拋妻棄子,乃至欠債不還;夏嘎大學(xué)文化的女兒對此竟持支持態(tài)度,還因“挪用公款鋃鐺入獄”。老人無法接受兒女們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變化,最終離開人世,靈魂去尋找死去的善良誠實(shí)的丈夫。扎西才讓的《牧羊人的愛情》、索朗達(dá)爾基的《拜活佛》、澤仁羅布的《騎在馬上》、龍仁青的《奧運(yùn)消息》等等也是類似文化沖突的鏡像。還有傳統(tǒng)身份與現(xiàn)代身份意識的沖突、城市文化與鄉(xiāng)村文化之間的沖突。尼瑪潘多的《紫青稞》由城鄉(xiāng)差異的對立寫到新一代藏民對現(xiàn)代生活的認(rèn)知與接受,在傳統(tǒng)身份崇拜意識瓦解的過程中,展現(xiàn)藏區(qū)牧民在巨大的現(xiàn)代文化變遷中的徘徊、掙扎、醒悟和無奈。她的《城市的門》、白瑪娜珍的《拉薩紅塵》也都如此。也有農(nóng)牧文化觀與商業(yè)經(jīng)濟(jì)文化觀的沖突。澤仁羅布《河流的方向》寫康巴藏地小鎮(zhèn),民風(fēng)淳樸、善良、真誠。當(dāng)商業(yè)經(jīng)濟(jì)大潮興起后,民風(fēng)大變。人們?yōu)閽旮噱X拋棄傳統(tǒng),制賣假蟲草,給積壓的松茸“美容”作假,塞鋼釘鐵絲等。科尼倉?索朗達(dá)爾基《信與不信的》、康巴作家群以康人署名的接力小說《彎彎月亮溜溜城》也有這方面的揭示。還有反映女性意識的覺醒與女性生存困境的沖突。何延華的《喬莊新年紀(jì)事》寫了藏區(qū)農(nóng)村女性進(jìn)城打工后所遭遇的種種困境與不幸,以及她們在傳統(tǒng)和陋俗之間的抗?fàn)幣c覺悟。新世紀(jì)藏區(qū)藏族女作家的創(chuàng)作大多都呈現(xiàn)了這方面的特點(diǎn)。白瑪娜珍的《復(fù)活的度母》、《拉薩紅塵》、多吉卓嘎的《藏婚》、《尼瑪石上》等即是如此。
在現(xiàn)代意識燭照下,藏區(qū)藏族作家深知“文化沖突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并不一定是壞事,因?yàn)樗谑聦?shí)上改變著文化的結(jié)構(gòu),改善著文化的形態(tài)和內(nèi)容,推動著文化向前發(fā)展。”[4](P.183-184)所以,他們的創(chuàng)作反映出對藏區(qū)文化沖突的審視態(tài)度也是客觀、理性和審慎的。
其一,他們能以理性的眼光審視文化沖突的根祗,評s文化沖突的本質(zhì)。《藏婚》將文化沖突定位在現(xiàn)代婚姻與情感形式的召喚(即好好的朋友蓮與活佛洛桑間專一溫馨的愛情示范),個人主體意識的覺醒(嘉措在大城市拉薩經(jīng)商后接受的現(xiàn)代人生觀、愛情觀)與頑固的傳統(tǒng)家庭生活結(jié)構(gòu)與方式間的博弈。嘉措為尋找屬于個人的專一愛情而背叛兄弟共妻的家庭;女主人公卓嘎在面對丈夫背叛家庭與自個尋愛的態(tài)度以及好好對愛情的執(zhí)意追求下,而產(chǎn)生愛情獨(dú)有的渴望。卓嘎的女性意識萌芽,意味著藏區(qū)傳統(tǒng)家庭生活模式在新與舊的人生觀、婚戀觀的碰撞中解體,建立新型的婚戀觀和新型家庭模式是文明進(jìn)步的必然結(jié)果①。
其二,作家們在文化沖突的現(xiàn)象揭示和文化意義的價(jià)值評估方面能取發(fā)展進(jìn)步的姿態(tài),超越民族性傳統(tǒng)型的思維邏輯,而獲得現(xiàn)代性視野,更富人類性情懷。萬瑪才旦的《第九個男人》寫一藏族女性在各種物質(zhì)和精神的誘惑下,命運(yùn)的起起伏伏。這個女人對生命和性的態(tài)度,他的男人對她的態(tài)度無不透出一種豁達(dá)而開放的胸懷。雖然藏族對性的觀念較為開放,但女人為個人的欲望而放逐性,卻能取得丈夫的理解或大度,其人性關(guān)懷的量度遠(yuǎn)遠(yuǎn)超過個人情感的尺度。女人違背民族傳統(tǒng)的價(jià)值選擇,男人對這種價(jià)值選擇的認(rèn)肯都是對“生命第一“這種現(xiàn)代人類意識的趨同。
其三,由于各種主客觀條件的局限或影響,比如長期以來文學(xué)創(chuàng)作形成的對正面性肯定,對負(fù)面性回避的態(tài)度或者作家深入生活的局限,又或者傳統(tǒng)創(chuàng)作中常見的“團(tuán)圓意識”的影響等等,藏區(qū)藏族作家面對尖銳或激烈的文化沖突,往往會以一種傳統(tǒng)的甚或宗教的態(tài)度規(guī)避沖突的尖銳性、復(fù)雜性,而以一種圓融、柔性甚至簡單的文化漸變形式給作品或人物留一個圓滿的結(jié)束。澤仁羅布的《騎在馬上》寫藏民嘎絨在草原文化轉(zhuǎn)型過程中,由牧民到馬背郵遞員,再回到領(lǐng)工資的牧民身份。主人公做馬背郵遞員時(shí)精神需求獲得極大滿足――受到大家的歡迎、敬重;物資上也獲得極大滿足――成為大家羨慕的領(lǐng)工資的“公家人”。然而經(jīng)濟(jì)發(fā)展起來,各鄉(xiāng)修通了公路。馬背郵遞工作被機(jī)械化三輪摩托車替代。嘎絨雖然有退休工資,但生活又回到草原牧民模式。嘎絨的失落和傷心并沒有被放大或縮小。他每月仍按當(dāng)年郵局給大黃馬的待遇――“自己掏錢買三十斤胡豆”喂馬,以此安撫那個失落的心。文化變遷沒有沖突、沒有敲打,主人公的人生、命運(yùn)、性格、情感的變化有起有落,但總是柔性的、隨應(yīng)的、和風(fēng)細(xì)雨般的。多吉卓嘎《藏婚》里的人物最終都有了文化意識的覺醒和生活形態(tài)的改變,都找到了自己美好的或者合適的歸屬。作品傳遞的信號似乎通過文化沖突達(dá)到文化轉(zhuǎn)型和文化進(jìn)步既是必然的也是簡單容易的。文化沖突或許還應(yīng)該有更為強(qiáng)烈甚至急風(fēng)暴雨式的表現(xiàn),文化沖突的結(jié)果也有可能是悲劇的。但作家們憑著民族文化奠定的精神信念和生活處理藝術(shù)可以將此處理得平淡、柔和,圓融。或者將沖突的劇烈、殘酷以藏族獨(dú)特的宗教式的方法稀釋,或者放在更加現(xiàn)代性的思考場閾作開放性的處理。《前方有人等她》中夏嘎老太的現(xiàn)實(shí)困境,在生命的最后被靈魂“尋夫”的愿景消解,沒有悲傷,只有圓滿。《紫青稞》中的文化沖突是劇烈的殘酷的,傳統(tǒng)無法挽回,鄉(xiāng)村終究失守。作者為消解這種殘酷和絕望,總是在現(xiàn)代與傳統(tǒng),宗教與世俗,鄉(xiāng)村與城市間盡力地調(diào)和著矛盾沖突,將絕望隱沒而凸現(xiàn)希望。于是作品中的人物各得其所,因果分明,希望與絕望同行。正是如此,所以當(dāng)主人公們在文化變遷中不適、無助、落寞甚至無所改變時(shí),作家們流露的感情往往總是一縷淡淡的、輕輕的憂郁、傷感或者遺憾。像阿來的《三只蟲草》、龍仁青的《奧運(yùn)消息》、扎西才讓的《牧羊人的愛情》都是以此態(tài)度化解沖突,表現(xiàn)出現(xiàn)代性的寬廣胸懷和理性智慧。
三、現(xiàn)代國家意識關(guān)照下的多民族文學(xué)書寫
百年以來我們由文化意識上的現(xiàn)代中國多民族國家共同體的建構(gòu)想象,進(jìn)而在體制上完成了中國多民族現(xiàn)代國家的建構(gòu)。“一旦某個國家在政治上成立,得到國際社會承認(rèn),那么無論這個國家內(nèi)部有多少民族(種族)、宗教、語言和完全不同的文化歷史,生活習(xí)俗,它都應(yīng)該被視為一個民族”[5](P.29) 這是在政治意義上闡釋的多民族現(xiàn)代國家概念。這個概念確定了政體上的國家完整性。從人類文化發(fā)展的客觀規(guī)律看,“文化不僅有排他性,也有融合性。特別是當(dāng)有不同文化的族群雜居在一起時(shí),他們的文化必然相互吸收、融合、涵化,發(fā)生內(nèi)容和形式上的變化,逐漸整合為一種新的文化體系。”[3](P.305)對中國而言,這種新的文化體系即中華多民族文化體系。因此,民族同一,發(fā)展進(jìn)步,交流融合已成新世紀(jì)文化發(fā)展的大趨勢。在此大趨勢下,多民族文學(xué)書寫也成為藏區(qū)藏族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重要維度。就如中國古典文學(xué)隨歷史文化的發(fā)展變遷而逐漸融匯、壯闊、豐滿一樣,各個少數(shù)族群作家的創(chuàng)作已經(jīng)匯入中華多民族書寫的文學(xué)共同體中,構(gòu)成了中華民族文學(xué)多姿多彩的斑斕景象。所以,從某種特定意義上看,藏區(qū)藏族文學(xué)創(chuàng)作必然是中華多民族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構(gòu)成部分。與以前相比,新世紀(jì)藏區(qū)藏族作家們在關(guān)注和融入多民族文學(xué)創(chuàng)作方面是取了積極進(jìn)步的姿態(tài)。他們的多民族書寫既反映了作家們基于現(xiàn)性的民族認(rèn)同意識,也證明通過文化沖突,文化變遷必將達(dá)到文化發(fā)展,文明進(jìn)步的現(xiàn)代科學(xué)規(guī)律。
新世紀(jì)藏區(qū)文學(xué)創(chuàng)作呈現(xiàn)的“多民族書寫”概念主要含蘊(yùn)了四個層面的意義。
一是漢族作家或其他族群作家寫藏區(qū)和藏族同胞生活的作品。比如,非藏裔作家有藏區(qū)生活經(jīng)驗(yàn),或有長期藏區(qū)生活經(jīng)歷,或者了解藏區(qū)歷史、文化、生活,擅長寫作藏區(qū)題材,而創(chuàng)作的作品。馬麗華、泱風(fēng)、劉金元的散文;裘珊珊、何馬、楊志軍的小說以及彝族作家俄尼牧斯寫藏區(qū)生活的作品等等即屬此類。這類藏區(qū)書寫看重的是異域風(fēng)情形貌的涉獵,給予讀者的是一幅文化場景的繪制或一段生命歷程的體驗(yàn)。對作者而言,他們更想傳達(dá)的是中華民族地域廣袤,族群眾多,生活樣態(tài)豐富的文學(xué)認(rèn)知。所以文中不乏對藏地景物風(fēng)土、對藏民生活與歷史的溢美性書寫或獵奇性書寫。于是,《藏地密碼》帶給人們無盡想象和渴望;《藏獒》因動物而及人,延伸了對一個邊地族群無由的好感;《我在天堂等你》更是從一個政治命題上,開掘出對藏地、生命、愛情、民族的復(fù)調(diào)意蘊(yùn),使艱苦的生活、苦澀的愛情在藏區(qū)綻放幸福的花兒。
二是藏區(qū)藏族作家寫非藏區(qū)或者非藏族生活的作品。比如阿來的《夢魘》,寫的是現(xiàn)代內(nèi)地都市和現(xiàn)代人的困惑,并不涉及特定藏區(qū)或漢區(qū)生活。仁真旺杰的創(chuàng)作或者寫彝區(qū)生活和彝藏交融,或者寫居處藏區(qū)的其他民族的生活。如《姨父汪懷明》、《藏寨里的一雙漢族老人》。澤仁羅布的小說《舉起你的手》寫了現(xiàn)代城市一對父女(族裔不明)在價(jià)值選擇上的沖突,并未呈現(xiàn)任何藏區(qū)生活經(jīng)驗(yàn)或藏區(qū)藏族生活痕跡。但是這類書寫更多地表現(xiàn)了現(xiàn)代文化帶給民族融合的客觀現(xiàn)實(shí),以及不同民族交融的現(xiàn)實(shí)必然性。
三是藏區(qū)藏族作家寫藏區(qū)藏族生活或藏族與其他族群共同生活的作品。由于民族交流、融合的歷史和現(xiàn)實(shí),藏族作家的創(chuàng)作不僅僅寫到本族群的生活、歷史、文化,也會自然而然地寫到生活中“他者”族群在藏區(qū)的生活以及藏裔族群與之交流、融合、涵化的過程、形態(tài)等等。比如達(dá)真的《康巴》、《命定》、《落日時(shí)光》、《放電影的張丹增》、澤仁羅布的《空隙》、阿來的《瞻對》《空山》等等都寫了藏區(qū)多民族交流融合,共同發(fā)展進(jìn)步的歷史與現(xiàn)實(shí);多吉卓嘎的《藏婚》寫了漢族女子與藏族男子(好好與嘉措)的愛情糾葛,也寫了漢族女子蓮與藏族活佛洛桑的美好婚姻。
四是藏裔作家與多族性作家寫藏區(qū)的生活。比如,以康人署名的《彎彎月亮溜溜城》就是由二十一位分屬漢、藏、彝、回、土家等不同族裔的作家接力創(chuàng)作的反映康巴藏區(qū)生活和康巴人情感的長篇小說。還有的作家身份是多重的,父輩或祖輩早已實(shí)現(xiàn)了民族混血的事實(shí)。在藏區(qū)的藏族作家中有不少的出身背景屬于藏漢融合,藏苗融合、藏羌融合、藏回融合等等多種民族混融情況,還有的是出身于藏地成長于內(nèi)地,有的出身成長于內(nèi)地生活創(chuàng)作于藏地,以及祖輩以來就是多民族雜居的情況。如此即給他們的多民族書寫提供了豐富的文化源泉和多彩的民族生活摹本,為他們夯實(shí)了多民族書寫的文學(xué)基礎(chǔ)。
本文論述的范疇主要指第三、第四層面的情況。藏區(qū)藏族作家們的多民族書寫有客觀歷史和現(xiàn)實(shí)的情景規(guī)定:比如封建時(shí)代對藏區(qū)治理的歷史,藏族與漢(或多民族)經(jīng)貿(mào)活動形成的民族雜居,的政改、后的民族交流融合,改革開放后尤其新世紀(jì)以來越來越發(fā)達(dá)進(jìn)步的藏區(qū)現(xiàn)實(shí)等等。對生活的客觀摹寫是多民族書寫的自然因子,“見與不見,她都在那里”,客觀無法回避,多民族書寫也不可回避。另一方面,現(xiàn)代視域的建立,“和合同一”國家情懷的形成以及檢省歷史、審視現(xiàn)實(shí)后獲得的理性思考,促成了作家們多民族書寫的自覺性,也讓他們擺脫了狹隘的文學(xué)視域和思想上民族固封自閉的文學(xué)思維。《瞻對》在寫清政府對瞻對地區(qū)先統(tǒng)而不治,后“改土歸流”民族同融時(shí),作家的識見跳出了狹隘的民族本位視界,客觀地評斷了通過政治治理手段,獲得民族認(rèn)同以及民族認(rèn)同對社會發(fā)展,文明進(jìn)步的積極意義。“民族主義首先是一條政治原則,它認(rèn)為政治的和民族的單位應(yīng)該是一致的。……使他們成為民族的,正是他們對這種伙伴關(guān)系的相互承認(rèn),而不是使這個類別的成員有別于非成員的其他共同特征。”[6](P.1)在阿來的《瞻對》中顯然反映的正是這種20世紀(jì)以來代表著先進(jìn)思想理論的經(jīng)典民族認(rèn)同思維。達(dá)真的《康巴》,漢、藏、回不同的民族交織在藏地歷史的闊大背景中,在英雄主義、心靈史詩、民族融合的多重奏里,回蕩著民族和睦友愛的笛音。其《命定》寫到藏、漢子弟在保國抗日的滇緬前線,共同收復(fù)騰沖,攻克松山,抗擊外敵,為中華民族國家捐軀。生命的價(jià)值定格在多民族家國的完整、鞏固,人類命運(yùn)的自由自主,達(dá)真的內(nèi)心一定鼓蕩著一面中華民族國家大義的旗幟。多吉卓嘎的《藏婚》更是將最好的家庭模式,最美的生命形態(tài)賦予給藏漢結(jié)合、藏漢融合的民族想象,漢族姑娘蓮和活佛洛桑的美滿婚姻所暗示和象征的意義是不言而喻的。
綜上所述,新世紀(jì)藏區(qū)文化轉(zhuǎn)型使藏區(qū)藏族文學(xué)創(chuàng)作有了突破的契機(jī)。構(gòu)建現(xiàn)代視域,關(guān)注文化變遷,呈現(xiàn)多民族融合現(xiàn)實(shí)成為藏區(qū)藏族作家的創(chuàng)作自覺。在現(xiàn)代視域下藏區(qū)藏族作家們理性地審視歷史,面對現(xiàn)實(shí),開掘思想,書寫人類意識,抒發(fā)家國情懷。這一切構(gòu)成新世紀(jì)藏區(qū)藏族文學(xué)豐富而現(xiàn)代的新風(fēng)貌。
注釋:
①事實(shí)上文化沖突的存在是長久而復(fù)雜的。英籍華人作家書云的紀(jì)事文學(xué)《一年》寫到2008年他們在距拉薩不遠(yuǎn)的江孜縣駐地拍片一年,現(xiàn)實(shí)中接觸到的一妻多夫制家庭并不少見。這種形式的家庭在改革開放前大多禁止了,可改革開放后又在民間普遍出現(xiàn)。類似漢族過年放爆竹的習(xí)俗禁而不絕,卷土重來。藏族女作家格央在其散文集《雪域的女兒》之《八廓街的康巴女子》中也寫到拉薩城里經(jīng)商的女性吉央、宗措的嫂子等新世紀(jì)的藏族女性都組成了一妻多夫家庭。這種情況恰恰說明文化存在的頑固性,文化改造的艱巨性。
參考文獻(xiàn):
[1][英]斯蒂夫?芬頓.族性[M].勞煥強(qiáng),等,譯.北京:中央民族大學(xué)出版社,2008.
[2]阿來.看見[M].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2011.
[3]司馬云杰.文化社會學(xué)[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xué)出版社,2001.
[4]陳華文.文化學(xué)概論[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
藏族的文學(xué)藝術(shù)范文第4篇
Abstract: Turkish language and culture is the important one of the treasures of the Chinese culture, is also advantage cultural resource of developing local cultural industries in Qinghai. Enhancing the protection of the national languages and culture inheritance is import to inherit and promote excellent cultural spirit, also contribute to better promote harmoniou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關(guān)鍵詞: 土族;語言與文化;保護(hù)與傳承;意義
Key words: Turkish;language and culture;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significance
中圖分類號:H231 文獻(xiàn)標(biāo)識碼:A 文章編號:1006-4311(2013)19-0302-02
0 引言
語言是文化的載體,中國是一個多民族語言的大家庭。各民族不同的語言承載著不同文化風(fēng)格,共同構(gòu)成了中華民族大文化。繁榮民族文化,引領(lǐng)文明建設(shè),促進(jìn)文化大發(fā)展大繁榮始終是我國民族事業(yè)的重中之重。青海省地處青藏高原,也是一個多民族的省份,因歷史原因生活在該地區(qū)的各民族既相互交融,又在長期的歷史歲月里形成了展現(xiàn)自我特色的語言與文化,其中土族獨(dú)特的語言文化和風(fēng)俗習(xí)慣,成為了青海地方富有特色的人文景觀之一。
1 土族語言與文化的歷史結(jié)晶
土族是青海是世居少數(shù)民族之一。主要分布在海東地區(qū)互助土族自治縣、民和回族土族自治縣、西寧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縣、黃南藏族自治州同仁縣,及樂都、門源等縣,散居在青海省各州縣。土族有獨(dú)立的民族語言,屬阿爾泰語系蒙古語族。土族語言內(nèi)部分為互助、民和和同仁3個方言區(qū)。土族沒有本民族傳統(tǒng)文字,在20世紀(jì)50年代國家對少數(shù)民族語言進(jìn)行大規(guī)模調(diào)查研究的基礎(chǔ)上,于 1979年創(chuàng)制了以拉丁字母為字母形式的拼音文字,現(xiàn)正在互助土族自治縣試行。土族文字為搶救、繼承和發(fā)揚(yáng)本民族傳統(tǒng)文化起到了其他文字無法替代的作用,同時(shí)也成為土族人學(xué)習(xí)漢語文和其他民族語文的重要工具。
土族也是一個能歌善舞的民族。在民族自身的歷史發(fā)展與演進(jìn)的過程中,也產(chǎn)生了大批相應(yīng)于本民族語言優(yōu)秀的文化藝術(shù)作品。最富有代表性的莫過于學(xué)界公認(rèn)的土族民間文學(xué)藝術(shù),諸如互助等地的《陽世的形成》和《天地形成》、《打柴狼的故事》、《日蝕和月蝕的傳說》,以及民和三川土族傳唱著古老的《混沌周末歌》等神話故事,形象生動地反映了土族先民勇于開拓,堅(jiān)毅不屈的進(jìn)取精神。[1]土族“花兒”更是成為青海地區(qū)極具地方風(fēng)格的藝術(shù)形式,在高原之上艷艷盛開,如頗為流行的“土族令”、“互助令”、“尕馬兒令”、“繞三令”等,以及具有強(qiáng)烈民族特色的傳統(tǒng)情歌,如“嘎達(dá)古道”、“瑪森格”、“蒙古爾孔尼阿姑”等等,反映了土族人民樸實(shí)真摯的情感生活,[2]至今仍是田間地頭詠唱不斷地曲調(diào)。
土族的敘事長詩在世代相傳,口口相授的過程中,逐漸被保存下來的共有8個,其中互助地區(qū)七個、民和地區(qū)一個《混沌周末歌》。其中用土語演唱的5個:《太平哥兒》、《拉仁布與且門索》、《布柔尤》、《福羊之歌》;用漢語演唱的三個《祁家延西》、《混沌周末歌》和《登登瑪秀》。這些作品很好地反映了土族民族的歷史與民族豐富的情感生活。[3]
土族生活地區(qū)保留有一些人類古老的巫術(shù)活動。作為青海省特有民族重要的民俗文化禮儀,互助地區(qū)土族婚禮更是“涵蓋了土族人生活習(xí)俗、、審美藝術(shù)、倫理道德等多方面內(nèi)容,是土族傳統(tǒng)文化的綜合體現(xiàn)。”基于土族文化藝術(shù)的特點(diǎn),有學(xué)者明確指出,“土族在保留自身文化藝術(shù)特征的同時(shí),兼容漢、藏、蒙等民族文化,呈現(xiàn)出多元性、原始性、獨(dú)特性、宗教性、融合性和地域性等特點(diǎn)。”
2 土族語言使用與文化的現(xiàn)狀
隨著當(dāng)代經(jīng)濟(jì)文化發(fā)展,土族的民族語言與文化也在發(fā)生著有目共睹的變化。從土族語言使用現(xiàn)狀的調(diào)查來看,所發(fā)生的變化主要表現(xiàn)為以下幾方面:
第一、受漢文化的強(qiáng)勢影響與民族語言自身的特點(diǎn),土族語言使用的范圍越來越封閉,僅僅在本民族聚居地內(nèi)部使用土話,對外幾乎不說土話。第二,不同年齡,所受教育程度不同,對土族語言使用也出現(xiàn)不對等的現(xiàn)狀。年輕的一輩已然聽不懂老一輩的土話,老一輩人也很少繼續(xù)使用并教育下一輩人沿用過去時(shí)代的土話。文化程度越高的,使用土話的頻率也就越低。受時(shí)代新語詞的影響,在土話中找不到對應(yīng)的語音發(fā)音,出現(xiàn)借用漢語或藏語語音表達(dá)新詞語的現(xiàn)象,屢增不減。第三,在大通、黃南、民和、互助四地,因歷史原因,民族遷徙,土族同其他民族雜居、混居,致使一些地方的土族已經(jīng)完全不再使用本民族的語言,而轉(zhuǎn)用漢話或藏話,尤為明顯的是大通、黃南,民和與互助部分地區(qū)也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這種現(xiàn)狀。第四,基于語言經(jīng)濟(jì)的原則,大多數(shù)土族同胞從思想和民族心理情感上意識到使用本民族語言的重要性,但從現(xiàn)實(shí)的角度出發(fā),他們還是選擇更為優(yōu)勢的語言進(jìn)行交際與生活。
土族語言使用發(fā)生變化,也影響到了本民族傳統(tǒng)文化的傳承與保護(hù)。古老的土話只保存于世代相傳的口頭文學(xué)里,這些珍貴的民間文學(xué)藝術(shù)作品對年青的土族一代是陌生的,也是遙遠(yuǎn)的,所以保護(hù)的工作就落在了文化工作者的身上,借助印刷、錄音、攝像等現(xiàn)代媒體技術(shù),最初“活”的語言成為了“舊”的歷史。作為土族身份象征的各種傳統(tǒng)符號也在發(fā)生變化,尤以土族傳統(tǒng)服飾最為明顯,互助、樂都、大通一帶的土族服飾,雖仍保持傳統(tǒng)習(xí)俗,但也發(fā)生了變化。民和地區(qū)已基本漢化,同仁地區(qū)則已基本藏化。伴隨旅游業(yè)的發(fā)展,土族傳統(tǒng)文化也受到了嚴(yán)峻的考驗(yàn),已由最初富有特定文化意義的儀式活動演變發(fā)展為被展示、被娛樂的表演節(jié)目。
3 保護(hù)與傳承土族語言與文化的意義
文化是一個民族的根基,語言又是文化重要的載體,二者相互依存,共同體現(xiàn)著一個民族的文化色彩、審美情感和價(jià)值觀,以及民族的思想和情感。一旦一個民族的文化與語言逐漸消退,那么這個民族的情感、價(jià)值觀也會隨之消亡。在全球經(jīng)濟(jì)一體化的大趨勢之下,中華民族整體的文化都在承受著前所未有的壓力與挑戰(zhàn),如何更好地傳承與發(fā)展民族文化,即“維護(hù)多元文化的存在,保持和發(fā)展自己民族文化的主體性,可以說已經(jīng)成為當(dāng)今世界許多國家、民族最關(guān)切的一個問題。”
文化是一種軟實(shí)力。歷史上的土族也是在不斷吸收和融合了其他民族的先進(jìn)文化中逐步成就了自我的文化特色,這從土族的、民族服飾、飲食習(xí)慣、民俗活動與民間說唱文學(xué)藝術(shù)中都能看出端倪。因此,保護(hù)與傳承民族的語言與文化,就具有了時(shí)代的重要性與現(xiàn)實(shí)意義。
首先,加強(qiáng)民族語言與文化的保護(hù)與傳承,是土族在新時(shí)期不斷求發(fā)展的根本所在。就土族的語言與文化現(xiàn)狀而言,傳承老輩藝人的語言與文化傳統(tǒng),激發(fā)起民族自豪感與自信心,從而在享有民族物質(zhì)家園的同時(shí),又能保護(hù)民族精神家園,是土族立于民族之林的根本。其次,加強(qiáng)民族語言與文化的保護(hù)與傳承,是對中華民族優(yōu)秀精神的繼承與發(fā)揚(yáng)。土族的語言與文化不單單是土族特有的思維與情感的體現(xiàn),其中也包涵和容納了其他民族的文化思想與情感,使得土族民族文化呈現(xiàn)出了多元性的特點(diǎn)。因此,傳承本民族文化,是在傳承土族優(yōu)秀文化基礎(chǔ)上,發(fā)揚(yáng)著中華民族的優(yōu)秀精神。最后,加強(qiáng)民族語言與文化的保護(hù)和傳承,有助于更好地開發(fā)富有民族特色文化產(chǎn)業(yè)。自2005年以來,互助的《土族婚禮》、民和三川地區(qū)土族納頓、《土族酩餾酒》等多個項(xiàng)目被先后批準(zhǔn)為國家級、省級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保護(hù)項(xiàng)目。眾多的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項(xiàng)目為文化產(chǎn)業(yè)的發(fā)展提供了豐富的內(nèi)容。由此,加強(qiáng)土族語言與文化的保護(hù)、傳承,才能更好地開發(fā)和創(chuàng)新出符合于時(shí)代文化之需的物質(zhì)產(chǎn)品,從而進(jìn)一步推動民族文化產(chǎn)業(yè),帶動地方經(jīng)濟(jì)與文化的發(fā)展。
參考文獻(xiàn):
[1]邢海燕.土族口頭傳統(tǒng)的確認(rèn)[J].西北民族大學(xué),2005(4):18-20.
[2]喬生菊.淺談土族文學(xué)藝術(shù)[J].中國土族,2010(2):1.
藏族的文學(xué)藝術(shù)范文第5篇
【關(guān)鍵詞】民族民間文學(xué)作品 著作權(quán) 平衡 保護(hù)
隨著現(xiàn)代網(wǎng)絡(luò)科技的發(fā)展,世界文化交流融通越來越便捷,而個性化、多樣化的民族民間文化正猶如城市的風(fēng)景,逐漸被統(tǒng)一化、制式化。對待民族民間文化,是任其自生自滅還是予以保護(hù)?如果對其予以保護(hù),必然涉及成本問題,是否得不償失?在對這些問題的思考中,應(yīng)該意識到,民族民間文化是我國的一項(xiàng)“比較優(yōu)勢”,具有巨大的開發(fā)價(jià)值。中國歷史悠久、民族眾多,至今還存在很多相對落后和封閉的區(qū)域能夠“原汁原味”地保存我們底蘊(yùn)豐厚的民族民間文化。在文化領(lǐng)域,只有個性的才更鮮活,才更有價(jià)值,因此這一豐富的資源,正體現(xiàn)了我國文化上的“比較優(yōu)勢”。我國在“自主知識產(chǎn)權(quán)”的擁有及利用上并不占優(yōu)勢,因?yàn)榘l(fā)明專利、商標(biāo)、軟件等知識產(chǎn)權(quán)主要為西方發(fā)達(dá)國家所掌握,所以,我們就更應(yīng)將目光投向自己占據(jù)比較優(yōu)勢的項(xiàng)目上,重視民間文學(xué)藝術(shù)作品的法律保護(hù)。即使對民族民間文化進(jìn)行保護(hù)可能需要付出成本,但對其進(jìn)行開發(fā)利用且利用得當(dāng),就能創(chuàng)造更為可觀的價(jià)值。比如美國迪斯尼上映的中國元素的動畫片《花木蘭》《龜兔賽跑》《功夫熊貓》等,均選取了我國民族民間文化中的優(yōu)秀題材,并獲得了商業(yè)的成功。況且,就成本論成本,我們亦認(rèn)為,只要制度設(shè)計(jì)得當(dāng),成本是可以得到控制的,對民族民間文化的利用將更加科學(xué)有序。因而,在對民族民間文化進(jìn)行保護(hù)時(shí),對其保護(hù)制度的研究,就成為一個非常重要的課題。在此,本文將選取民族民間文化中的精粹——民族民間文學(xué)作品,就其著作權(quán)保護(hù)法律制度的相關(guān)基礎(chǔ)理論問題進(jìn)行探討。
一 民族民間文學(xué)作品的界定
1.民族民間文學(xué)作品的概念及內(nèi)涵
對民族民間文學(xué)作品進(jìn)行界定,首先涉及到什么是民族的問題,對此學(xué)界向來沒有統(tǒng)一的認(rèn)識。認(rèn)為,民族是“人們在歷史上形成的一個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jīng)濟(jì)生活以及表現(xiàn)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zhì)的穩(wěn)定的共同體”。以該定義為基礎(chǔ),我們認(rèn)為民族民間文學(xué)作品是指通常情況下作者不明確,且沒有固定化的有形載體,但有充分理由推斷出自某社會共同體并世代流傳的屬于民族文化遺產(chǎn)的藝術(shù)作品。
在世界立法例上,對民族民間文學(xué)作品所采用的稱謂和對其內(nèi)涵的理解不盡相同。有的定義為“民間文學(xué)”,如較早在“跨國版權(quán)法”中保護(hù)民間文學(xué)的非洲知識產(chǎn)權(quán)組織,該組織認(rèn)為,受版權(quán)法保護(hù)的民間文學(xué)包括:“一切由非洲的居民團(tuán)體所創(chuàng)作的、構(gòu)成非洲文化遺產(chǎn)基礎(chǔ)的、代代相傳的文學(xué)、藝術(shù)、科學(xué)、宗教、技術(shù)等領(lǐng)域的傳統(tǒng)表現(xiàn)形式與產(chǎn)品。”在這一定義中,民間文學(xué)的范圍是十分寬泛的;有的定義為“民間文學(xué)藝術(shù)作品”,如俄羅斯1993 年7 月的《版權(quán)法》,并且將這類作品的范圍劃得較為狹窄;還有稱為“土著居民的藝術(shù)作品”、“通俗文學(xué)”、“俗文學(xué)”......而我國的著作權(quán)法將這部分作品的名稱界定為“民間文學(xué)藝術(shù)作品”。事實(shí)上,考察立法目的,不論該類立法所采用的名稱是什么,我們認(rèn)為這都是對民間文化資源的界定,是對應(yīng)于版權(quán)法上的作品的。版權(quán)法上的作品均是對現(xiàn)有知識的一種具有新穎性的思想表達(dá)方式,而民族民間文學(xué)作品即為“現(xiàn)有知識”中的一種重要資源,如果說版權(quán)法的作品是“流”的話,民族民間文學(xué)作品則為“源”。目前世界上許多國家,尤其是第三世界國家立法保護(hù)民族民間文學(xué)作品,正是對“源”與“流”公平分配問題上的重新思考。這一來自于第三世界國家的聲音已為國際社會所重視,世界知識產(chǎn)權(quán)組織(WIPO)于2000 年成立了“知識產(chǎn)權(quán)與遺傳資源、傳統(tǒng)知識和民間文藝政府間委員會(以下簡稱IGC)”,以討論“產(chǎn)生于遺傳資源的獲取和惠益分享、傳統(tǒng)知本文為2007~2008 年度云南省學(xué)習(xí)十七大精神哲學(xué)社會科學(xué)規(guī)劃課題《民族民間文學(xué)作品之著作權(quán)保護(hù)研究》課題的階段性成果識(不論是否與遺傳資源有關(guān))的保護(hù)、民間文學(xué)藝術(shù)表達(dá)的保護(hù)中的知識產(chǎn)權(quán)問題”。迄今為止,IGC 的調(diào)研成果之核心內(nèi)容就是為傳統(tǒng)知識(TK)和民間文藝(TCEs)。而本文所探討的民族民間文學(xué)作品,其內(nèi)涵正與IGC 所提出之TCEs 所契合。
2.民族民間文學(xué)作品的外延
同民族民間文學(xué)藝術(shù)作品的定義一樣,由于其目種實(shí)繁,其范圍的界定至今也尚無具有公信力的標(biāo)準(zhǔn),根據(jù)《保護(hù)民間文學(xué)表達(dá)形式、防止不正當(dāng)利用及其侵害行為的國內(nèi)法示范法條》第二條的規(guī)定,民間文學(xué)藝術(shù)作品主要包括下列內(nèi)容:(1)口頭表達(dá)形式,諸如民間故事、民間詩歌及民間謎語;(2)音樂表達(dá)形式,諸如民歌及器樂;(3)活動表達(dá)形式,諸如民間舞蹈、民間游戲、民間藝術(shù)形式或民間宗教儀式(這些形式不論是否已經(jīng)固定在有形物上);(4)有形的表達(dá)形式等。
二 著作權(quán)保護(hù)的涵義
著作權(quán),也稱版權(quán),是法律賦予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等民事主體的一種特殊的民事權(quán)利,是作者基于對特定的作品依法享有的專有權(quán)利,是作者及其他著作權(quán)人對文學(xué)、藝術(shù)、科學(xué)作品等作品所享有的人身權(quán)以及全面支配該作品并享受其利益的財(cái)產(chǎn)權(quán)的總稱。
著作權(quán)包括人身權(quán)和財(cái)產(chǎn)權(quán)兩項(xiàng)內(nèi)容。著作權(quán)法中的人身權(quán)不同于民法概念上的人身權(quán)。這種權(quán)利是與作者人身密不可分的。從人身權(quán)的起源看,18 世紀(jì)末,在資產(chǎn)階級的天賦人權(quán)思想的影響下,德國著名哲學(xué)家康德等人提出了作品是人格權(quán)、人身權(quán)的一種延伸權(quán)利的觀點(diǎn)。可以說,人身權(quán)是人權(quán)觀在著作權(quán)領(lǐng)域的體現(xiàn)。我國著作權(quán)法規(guī)定,著作權(quán)中的人身權(quán)包括:發(fā)表權(quán)、署名權(quán)、修改權(quán)、保護(hù)作品完整權(quán)。著作權(quán)中的財(cái)產(chǎn)權(quán)是指能夠給著作權(quán)人帶來經(jīng)濟(jì)利益的權(quán)利。這種經(jīng)濟(jì)利益的實(shí)現(xiàn),要依靠著作權(quán)人對作品使用才能獲得。根據(jù)我國《著作權(quán)法》的規(guī)定,著作權(quán)的財(cái)產(chǎn)權(quán)是指著作權(quán)人通過復(fù)制、發(fā)行、出租、展覽、表演、放映、廣播、信息網(wǎng)絡(luò)傳播、攝制或者改編、翻譯、匯編等方式使用作品并由此獲得報(bào)酬的權(quán)利,以及許可他人以上述方式使用作品,并由此獲得報(bào)酬的權(quán)利。
1.著作權(quán)保護(hù)的目的
研究著作權(quán)保護(hù)目的的重要的法律依據(jù)即著作權(quán)立法,綜觀世界各國法律中著作權(quán)保護(hù)的目的,我們發(fā)現(xiàn),不同國家有不同側(cè)重。大陸法系國家著作權(quán)保護(hù)的首要目的是保護(hù)作者的權(quán)利,著作權(quán)甚至被稱為作者權(quán),例如德國《版權(quán)法》一開始便有保護(hù)作者人身權(quán)的條款,并規(guī)定人身權(quán)不得轉(zhuǎn)讓;而英美法系國家除了重視對作者權(quán)利的保護(hù)以外,對其他利益主體和社會公共利益的保護(hù)也同樣看重。以美國為例,其《憲法》的著作權(quán)條款,從立法和司法方面考慮,授予作者著作權(quán)在美國被看成是服務(wù)于鼓勵智力作品的創(chuàng)作,而最終使公眾受益。從理論上說,至少公共利益優(yōu)先。
我國《著作權(quán)法》開篇第一條明確指出,制定著作權(quán)之立法目的是“為保護(hù)文學(xué)、藝術(shù)和科學(xué)作品作者的著作權(quán),以及與著作權(quán)有關(guān)的權(quán)益,鼓勵有益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物質(zhì)文明建設(shè)的作品的創(chuàng)作和傳播,促進(jìn)社會主義文化和科學(xué)事業(yè)的發(fā)展與繁榮”。有學(xué)者將該立法目的分為兩個層次,認(rèn)為著作權(quán)保護(hù)的直接目的是保護(hù)作者的著作權(quán)及相關(guān)權(quán)益,但終極目的卻是為了有利于作品的創(chuàng)造和傳播,以促進(jìn)社會整體利益。對于這樣的理解目前已不為學(xué)界主流觀點(diǎn)所認(rèn)同,法條的文意解釋并不能得出兩個遞進(jìn)層次的立法目的關(guān)系,我們認(rèn)為,著作權(quán)保護(hù)的目的在于協(xié)調(diào)和平衡兩種法律所同等尊重的價(jià)值——作者利益和社會的公共利益。
我國《著作權(quán)法》第十一條規(guī)定:“著作權(quán)屬于作者,本法另有規(guī)定的除外。”這一規(guī)定表明,作品著作權(quán)的原始?xì)w屬一般是作者,除非法律有特殊的規(guī)定。事實(shí)上,“著作屬于作者”是各國著作權(quán)法確認(rèn)著作權(quán)歸屬的一般原則。保護(hù)作者利益,從理論上看,是著作權(quán)領(lǐng)域?qū)θ藱?quán)的保護(hù)。作品是作者創(chuàng)造性勞動的成果,作者通過勞動獲得了對作品的產(chǎn)權(quán),由此獲得法律的保護(hù)。根據(jù)洛克的觀點(diǎn),“只要他使任何東西脫離自然所提供的和那個東西所處的狀態(tài),他就已經(jīng)摻進(jìn)他的勞動,在這上面摻加他自己所有的某些東西,因而使它成為他的財(cái)產(chǎn)。”而生命、自由、財(cái)產(chǎn)等即為人權(quán)的必要組成。從實(shí)踐上說,對作者權(quán)益的保護(hù),能夠轉(zhuǎn)化為作者創(chuàng)作的動力,激勵作者的創(chuàng)造性勞動,從而促進(jìn)社會的文明發(fā)展,這就轉(zhuǎn)向了著作權(quán)保護(hù)的另一目的——增進(jìn)社會公共利益。為了達(dá)到該二元利益平衡的目的,《著作權(quán)法》設(shè)置了種種法律制度。首先,法律承認(rèn)并保護(hù)作者對作品的專屬性,在某種程度上,或者說,是一種壟斷性利益,但同時(shí),為了使公眾能夠接觸并使用該作品,保護(hù)社會的公共利益,法律又對該壟斷性權(quán)利進(jìn)行必要的限制,設(shè)置了諸如著作權(quán)的保護(hù)期限、著作權(quán)的合理使用、法定許可等制度。
2.作品著作權(quán)保護(hù)的基本法律原則
受著作權(quán)法保護(hù)的作品應(yīng)當(dāng)符合下列原則:(1)思想與表達(dá)相區(qū)分原則,即著作權(quán)保護(hù)的對象限于通過一定載體表達(dá)出來的作品,而不延及思想、工藝、操作方法或數(shù)學(xué)概念之類;(2)獨(dú)創(chuàng)性原則,該原則要求作品應(yīng)由作者獨(dú)立創(chuàng)作,能夠體現(xiàn)作者的精神勞動和智力判斷,而非簡單的摹寫或材料的匯集;(3)平衡原則。如上所述,著作權(quán)法立法的目的是為了平衡作者和社會利益,促進(jìn)社會主義文化和科學(xué)事業(yè)的發(fā)展與繁榮,因此,受《著作權(quán)法》保護(hù)的作品不應(yīng)當(dāng)損害社會公共利益。
三 民族民間文學(xué)作品著作權(quán)保護(hù)之制度設(shè)計(jì)
根據(jù)上述對著作權(quán)保護(hù)的論述,我們發(fā)現(xiàn),現(xiàn)有的著作權(quán)制度在對民族民間文學(xué)作品保護(hù)上會產(chǎn)生很多問題,比如,著作權(quán)的一般主體是作者,但民族民間文學(xué)作品在通常情況下作者不明;民族民間文學(xué)作品的保護(hù)期限如何認(rèn)定等,基于此,有必要在著作權(quán)法的框架下,就民族民間文學(xué)作品的保護(hù)進(jìn)行新的法律解釋。
1.民族民間文學(xué)作品著作權(quán)保護(hù)之可能
正是由于民族民間文學(xué)作品著作權(quán)保護(hù)之種種困境,有學(xué)者提出,應(yīng)該脫離著作權(quán)法,創(chuàng)制新的法律制度以保護(hù)民族民間文學(xué)作品。筆者不同意這種觀點(diǎn),認(rèn)為著作權(quán)保護(hù)的是民族民間文學(xué)作品私權(quán)中的一個領(lǐng)域,利用現(xiàn)有成熟的版權(quán)制度進(jìn)行保護(hù)具有可行性,然而這并不意味著民族民間文學(xué)作品除此就沒有其他的保護(hù)方式了,事實(shí)上,對民族民間文學(xué)作品進(jìn)行法律的保護(hù)是多層次的,著作權(quán)保護(hù)只是其中的一個方面。
(1)民族民間文學(xué)作品的性質(zhì)決定其著作權(quán)保護(hù)的可能性。
知識產(chǎn)權(quán)與其他權(quán)利相區(qū)別的關(guān)鍵在于,其保護(hù)對象為非物質(zhì)性的信息,具有不同于物質(zhì)財(cái)產(chǎn)的重要特點(diǎn):①是一種精神財(cái)富,可以永久存續(xù);②必須以一定的物質(zhì)形式表現(xiàn)出來;③可以被有形載體固定并無限復(fù)制或重復(fù)使用;④可廣泛傳播;⑤可以同時(shí)被許多人使用;⑥不能用控制物質(zhì)財(cái)產(chǎn)的方式控制。考察民族民間文學(xué)藝術(shù)作品的本質(zhì)特征,正與信息的特征相契合,這就成為知識產(chǎn)權(quán)制度可以對民間文學(xué)藝術(shù)作品進(jìn)行保護(hù)的前提條件。當(dāng)然,也不是所有的信息都是知識產(chǎn)權(quán)的保護(hù)對象。能成為知識產(chǎn)權(quán)保護(hù)對象的信息還必須具有商業(yè)價(jià)值,能為民事權(quán)利主體支配并排斥他人干涉,即為一種專有權(quán)、對世權(quán)。
民族民間文學(xué)藝術(shù)作品的商業(yè)價(jià)值是顯而易見的,這里不再贅述。要探討的主要問題是,對這類信息的權(quán)利能不能成為一種對世權(quán)、支配權(quán)。根據(jù)對民族民間文學(xué)藝術(shù)作品的定義,該類作品雖然通常情況下作者不明,但卻有充分理由推斷出自某社會共同體,因而,如果將創(chuàng)作該類作品的社會共同體視為一個整體,該群體對其作品所享有的權(quán)利就是群體之外的任何人都不得侵害的,即其權(quán)利的效力可以對抗群體之外的一切人,為該群體所專有,是一種對世權(quán)。故,民間文學(xué)藝術(shù)作品只要是具有獨(dú)創(chuàng)性的智力創(chuàng)作成果,并通過一定載體所表達(dá),不損及社會公共利益,就能為《著作權(quán)法》所保護(hù)。
(2)我國立法思路決定民族民間文學(xué)作品著作權(quán)保護(hù)的可能性。我國《著作權(quán)法》第六條規(guī)定:“民間文學(xué)藝術(shù)作品的著作權(quán)保護(hù)辦法由國務(wù)院另行規(guī)定。”由此可知,在立法的思路上,法律已經(jīng)明確,民間文學(xué)藝術(shù)作品是我國著作權(quán)保護(hù)的客體,但鑒于其特殊性,具體的保護(hù)辦法又由國務(wù)院以行政法規(guī)予以規(guī)定。中國自20 世紀(jì)就一直組織進(jìn)行相關(guān)的立法工作,國家版權(quán)局在其他部委的支持下于1996 年起草了《民間文學(xué)藝術(shù)作品著作權(quán)保護(hù)條例》第一稿,該稿得到了世界知識產(chǎn)權(quán)組織的肯定。2002 年后,在1996 年基礎(chǔ)上國家版權(quán)局又起草了《民間文學(xué)藝術(shù)作品著作權(quán)保護(hù)條例》第二稿。根據(jù)《國務(wù)院辦公廳〈關(guān)于做好國務(wù)院2007 年立法工作計(jì)劃的意見〉和〈國務(wù)院2007 年立法工作計(jì)劃〉的通知》及《2007 年中國保護(hù)知識產(chǎn)權(quán)行動計(jì)劃》要求,2007 年9 月,國家版權(quán)局成立《民間文學(xué)藝術(shù)作品著作權(quán)保護(hù)條例》起草工作小組。目前民間文學(xué)藝術(shù)作品著作權(quán)保護(hù)的立法工作已經(jīng)列入國務(wù)院立法計(jì)劃當(dāng)中。
具有幾百年歷史的《著作權(quán)法》,是現(xiàn)代社會迄今創(chuàng)設(shè)的一種較好的平衡個人利益與社會整體利益的制度工具。只要稍微拓寬一點(diǎn)思路,將其用于平衡社會中的群體利益與社會整體利益,應(yīng)該是可行且有效的。對民間文學(xué)藝術(shù)作品進(jìn)行著作權(quán)保護(hù),不但可以利用原有的立法資源,節(jié)約立法成本,而且還可以借鑒著作權(quán)制度中已經(jīng)積累的豐富經(jīng)驗(yàn)。從這種意義上說,民間文學(xué)藝術(shù)作品的著作權(quán)保護(hù)又是必須的。
2.民族民間文學(xué)作品的主體
(1)民族民間文學(xué)作品主體的確定。民間文學(xué)藝術(shù)作品就主體而言,一般具有不特定性。這種“不特定性”就造成了著作權(quán)保護(hù)的困難。僅就學(xué)者們提出的各種建議而言,至少包括以下幾種:國家、民族和社區(qū)等。
第一,國家著作權(quán)人。筆者認(rèn)為,將國家籠統(tǒng)地認(rèn)定為民族民間文學(xué)作品的主體并不妥當(dāng)。
首先根據(jù)TRIPS 的規(guī)定,知識產(chǎn)權(quán)是一種私權(quán),其核心價(jià)值在于界定人們因智力成果及相關(guān)成就所產(chǎn)生的各種利益關(guān)系。直接將國家作為民族民間文學(xué)作品的主體,有公權(quán)與私權(quán)爭利之嫌。另外,既然已經(jīng)明確,《民間文學(xué)藝術(shù)作品著作權(quán)保護(hù)條例》應(yīng)該是《著作權(quán)法》的下位法,其就應(yīng)該遵循著作權(quán)法的基本原則,是對民族民間文學(xué)作品的一種私權(quán)保護(hù)方式。因此,學(xué)者提出,將國家視為民間文學(xué)藝術(shù)作品的權(quán)利主體這種具有濃厚國有制色彩的構(gòu)想是需要審慎對待的。
其次,如果籠統(tǒng)地把民間文學(xué)藝術(shù)作品的權(quán)利主體確定為國家,雖然在實(shí)踐中便于操作,而且可以突出民間文學(xué)藝術(shù)作品法律保護(hù)的主要作用——對抗由域外人士實(shí)施的、利用民間文學(xué)藝術(shù)營利,但卻不給予其發(fā)源地人民任何回報(bào)的利用,避免文化資源的流失。但應(yīng)考慮到,不合理利用并不局限于域外人士,還可能包括本國的、創(chuàng)作群體外的其他個人或組織。由國家統(tǒng)一行使權(quán)利的效率,可能不如由熟悉當(dāng)?shù)匚幕尘埃c傳統(tǒng)資源休戚相關(guān)的創(chuàng)作群體自行享有權(quán)利、行使權(quán)利、維護(hù)權(quán)利的效率高。當(dāng)然,在特殊情況下,亦不排除國家作為著作權(quán)人,我國著作權(quán)法對此也有規(guī)定。就民族民間文學(xué)作品來說,如作品的創(chuàng)作流傳出自哪個具體民族或地區(qū)不能確定,或者尚有爭議,可以由國家作為作品的著作權(quán)人。
第二,社區(qū)著作權(quán)人。在民族民間文學(xué)作品的歸屬問題上,主要有兩種認(rèn)定方式,即地區(qū)或民族,例如,中國三大英雄史詩之一的《格薩爾王傳》,誰都必須承認(rèn)它是屬于藏族的,同樣,彝族的《阿詩瑪》、傣族的《召樹屯》、白族戲劇吹吹腔、蒙古族薩滿祭詞......其民族歸屬是十分明了的。當(dāng)然,還有的民間文學(xué)藝術(shù)作品除以民族外,還根據(jù)地理范圍劃分歸屬,如田林壯劇,流傳于廣西百色地區(qū);馬隘壯劇,流傳于廣西德保縣馬隘等地;富寧壯劇,源于云南文山壯族苗族自治州富寧縣。而“社區(qū)”一詞是1887 年德國社會學(xué)家滕尼斯(F. Tonnies)提出的,不同的學(xué)者根據(jù)自己研究的需要,從不同層面、不同角度對社區(qū)進(jìn)行了界定,沒有公認(rèn)的定義。因此,筆者以“社區(qū)”概括之。本文所指社區(qū),即民族民間文學(xué)作品產(chǎn)生并流傳的某一個地區(qū)或某一個民族群體。
(2)著作權(quán)集體管理。以社區(qū)作為民族民間文學(xué)作品的主體,雖然易于界定,且能鼓勵各民族或地區(qū)整理保護(hù)自由的民間資源,但社區(qū)人數(shù)眾多,權(quán)利行使效力必然低下。根據(jù)美國奧爾森的“集體行為理論”,“有理性的、尋求自我利益的個人不會采取行動以實(shí)現(xiàn)他們共同的或集團(tuán)的利益”。如果別人采取了積極的行動,他自己亦不會排除于此共同利益(集體產(chǎn)品)之外的,而且如果別人付出成本,自己可以“搭便車”,坐享其成,何樂不為!故大集團(tuán)比起小集團(tuán)來,不能更有效地組織起集體行動。因此,在民族民間文學(xué)作品領(lǐng)域,和主體的界定相伴,必須提出此類作品著作權(quán)的集體管理辦法。
我國《著作權(quán)法》第八條規(guī)定了著作權(quán)的集體管理制度,實(shí)踐中,著作權(quán)集體管理組織如中國音樂作品著作權(quán)協(xié)會、中國文字作品著作權(quán)協(xié)會等已經(jīng)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保護(hù)著作權(quán)人利益,并促進(jìn)社會公眾著作權(quán)意識的目的,其運(yùn)作方式可以為保護(hù)民族民間文學(xué)藝術(shù)提供有益的借鑒。具體說,應(yīng)該成立非政府的民間組織來代為行使民族民間文化的相應(yīng)權(quán)利,以切實(shí)保護(hù)民族民間文學(xué)藝術(shù)發(fā)源地(族群)的集體利益。非政府組織依照法律規(guī)定成立、運(yùn)作,代表民族民間文化發(fā)源地(族群)對非發(fā)源地或族群之外的人使用、利用該民族文化依法行使相應(yīng)許可行為或收取合理費(fèi)用,代表參與訴訟、仲裁等活動。其收取的費(fèi)用用于該民族文化的保護(hù)與傳承。
(3)整理人、記錄人的著作權(quán)人地位。整理人、記錄人在=民族民間文學(xué)作品的搶救、傳承和保護(hù)工作中意義重大,但筆者認(rèn)為,整理人、記錄人不能成為民族民間文學(xué)作品本身的著作權(quán)主體,因?yàn)槊褡迕耖g文學(xué)作品是群體性勞動的成果,只能由相應(yīng)社區(qū)成為其著作權(quán)主體。至于整理人、記錄人如果在完成作品的時(shí)候付出了較大的創(chuàng)新性勞動,形成的則是基于民間文化之“源”的創(chuàng)作,是現(xiàn)行《著作權(quán)法》第九條所規(guī)定的“作品”,其自然啟動現(xiàn)有版權(quán)機(jī)制進(jìn)行保護(hù),但已不是對“民族民間文學(xué)作品”著作權(quán)的保護(hù)。如果整理人、記錄人只是忠實(shí)記錄或稍加整理,沒有創(chuàng)造性勞動的付出,對他們的保護(hù)或資金支持,則不在著作權(quán)法考慮的范疇,而是大的文化保護(hù)法應(yīng)該考慮的。
3.民族民間文學(xué)作品著作權(quán)的保護(hù)方式和權(quán)利內(nèi)容
(1)民族民間文學(xué)作品著作權(quán)的保護(hù)方式。鑒于民族民間文學(xué)作品主要是通過世代相傳的方式在某一群體存續(xù),其內(nèi)容持續(xù)處于動態(tài)發(fā)展過程中,因此,為了明確民間文學(xué)藝術(shù)作品的范圍,可以采取登記制度作為該類作品著作權(quán)的產(chǎn)生方式。我國國家版權(quán)局1994 年12 月頒布了《作品自愿登記試行辦法》,通過作者自愿的登記行為,對其著作權(quán)進(jìn)行形式上的確認(rèn),以進(jìn)一步明確著作權(quán)的歸屬,在發(fā)生著作權(quán)糾紛時(shí)也可作為初步證據(jù),從而最終達(dá)到維護(hù)作者和其他著作權(quán)人合法權(quán)益的目的。該辦法可作為民族民間文學(xué)作品著作權(quán)保護(hù)方式的法律依據(jù),而這實(shí)際上是與該類作品的國際保護(hù)方式相協(xié)調(diào)的。國際上對于該類作品的保護(hù)也采取了諸如登記、認(rèn)定等一系列制度,例如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人類口頭及非物質(zhì)遺產(chǎn)優(yōu)秀作品”的評審規(guī)則中,專門制定了作品的申報(bào)制度,其中規(guī)定申報(bào)的作品需附有作品所有者個人或群體認(rèn)可的文字、錄音、錄相或其他證明材料,無此等證明者不可申報(bào)。
采取登記制,一方面,可以明確作品的歸屬和具體范圍;另一方面,可以促進(jìn)權(quán)利主體對民間文學(xué)藝術(shù)作品的挖掘、整理工作,有利于國家對有重大價(jià)值的文學(xué)作品進(jìn)行管理,尤其是涉外使用的管理。
(2)民族民間文學(xué)作品著作權(quán)的內(nèi)容。民族民間文學(xué)作品著作權(quán)保護(hù)的目的在于,一方面,從法律上建構(gòu)文化領(lǐng)域“資源”和“創(chuàng)新”公平的分配機(jī)制,保障文化資源在被使用的情況下獲得合理的報(bào)酬;另一方面,以著作權(quán)保護(hù)的方式,從精神和經(jīng)濟(jì)兩方面激勵對民族民間文學(xué)作品的搶救性保護(hù)工作,明確作品的范圍和內(nèi)容,以利于作品的傳播,弘揚(yáng)中華傳統(tǒng)文化。因此,著作權(quán)保護(hù)的目的之一:“鼓勵作品的創(chuàng)作”,就顯然不適用于民族民間文學(xué)作品,這就決定了民族民間文學(xué)作品著作權(quán)的范圍和行使方式的特異性。
民族民間文學(xué)作品的著作權(quán)也包括人身權(quán)和財(cái)產(chǎn)權(quán)兩個部分,就人身權(quán)來說,筆者認(rèn)為其范圍只應(yīng)包括署名權(quán)、發(fā)表權(quán)和修改權(quán),而不包括保護(hù)作品完整權(quán)。因?yàn)橐獡尵群捅Wo(hù)民族民間文學(xué)作品,就必須鼓勵對作品的收集整理行為,以及在此之上的創(chuàng)新,而保護(hù)作品完整權(quán)顯然與該類作品的保護(hù)方式相沖突;就財(cái)產(chǎn)權(quán)來說,筆者認(rèn)為其行使的方式上不應(yīng)包括許可使用。民族民間文學(xué)作品應(yīng)強(qiáng)調(diào)自由使用,只要注明作品的出處,尊重著作權(quán)人的精神利益,并支付相應(yīng)費(fèi)用,滿足著作權(quán)人的財(cái)產(chǎn)利益即可使用。
4.民族民間文學(xué)藝術(shù)作品著作權(quán)保護(hù)期
筆者認(rèn)為,《著作權(quán)法》所規(guī)定“作者終身加死后五十年”的保護(hù)期限不適用于民族民間文學(xué)藝術(shù)作品。其一,從理論上講,如果把民間文學(xué)藝術(shù)作品的作者界定為作品的創(chuàng)作群體,根據(jù)目前著作權(quán)法保護(hù)期為作者生前加死后五十年的計(jì)算方法,只要創(chuàng)作民間文學(xué)藝術(shù)作品的群體一直存在,作品的保護(hù)期也就要一直延續(xù)下去,這實(shí)際上也就幾乎等于無期限保護(hù)了;其二,從民間文學(xué)藝術(shù)作品的特性來看,這類作品是代代相傳、世世延續(xù)的,處于始終動態(tài)的發(fā)展中,其“創(chuàng)作的階段性”難于認(rèn)定,這也決定了該類作品著作權(quán)的保護(hù)期應(yīng)該是無限的。
四 小結(jié)
通過對民族民間文學(xué)作品著作權(quán)保護(hù)法律制度的思考,我們認(rèn)為該類作品符合現(xiàn)行著作權(quán)法對作品的定義,現(xiàn)行《著作權(quán)法》之立法目的、對作品保護(hù)的基本原則及保護(hù)的方式等均基本適用于對民族民間文學(xué)作品的保護(hù)。但針對該類作品的特殊性,法律亦應(yīng)進(jìn)行相應(yīng)的調(diào)整,因此,應(yīng)在現(xiàn)行《著作權(quán)法》的框架下來建構(gòu)對民族民間文學(xué)作品的保護(hù)模式,制定專門法作為著作權(quán)法的下位法來具體調(diào)整該類作品的著作權(quán)保護(hù)。
注 釋
①鄭成思.世界各國的民間文學(xué)藝術(shù)保護(hù)況.cpo.cn.net/zscqb/lilun/t20020708_6772.htm
②管育鷹.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的法律保護(hù)探討. iolaw.org.cn/showNews.asp?id=17767
③田勝立.中國著作權(quán)疑難問題精析[M].武漢:華中理工大學(xué)出版社,1998:69、308
④ baike.baidu.com/view/4229584.htm
⑤馮曉青.著作權(quán)之立法宗旨研究.臺灣:月旦民商法雜志,2007(15)
⑥張玉敏.論知識產(chǎn)權(quán)的概念和法律特征.知識產(chǎn)權(quán)研究(第十三卷).北京:中國方正出版社,2003:177~180
⑦韋之、凌樺.傳統(tǒng)知識保護(hù)的思路[DB].cpo.cn.net/zscqb/lilun/t20020702_6427.htm
⑧〔美〕曼瑟爾·奧爾森.國家興衰探源[M].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