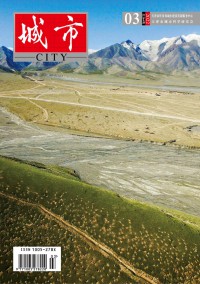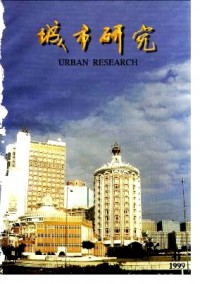城市歷史建筑文化解析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城市歷史建筑文化解析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一、城市建筑文化的內涵與意義
城市,就她實在的含義來說,就是人類生存的方式,以物質的和精神的空間顯現的人的文化,城市是人文的空間化。城市文化本質上涉及的是人與城市的關系,人、歷史、文化及其關聯,成為城市的靈魂。都市人類學認為,雖然城市文化作為人類文化發展的高級形態,比原始文化具有無比的豐富性。但是,現代城市文化概念的基本結構仍然是同一的:城市文化不過就是城市人格的表現,城市是人格化的主題空間,她映射著民族的、時代的、地域的與人格的輝光,是宗教的、哲學的、道德的、審美的等等文化的集中表現。具體來說,城市文化可以說是每一個時代的時尚的總匯,如建筑時尚、服飾時尚、飲食時尚、知識時尚等等,而能以不變的物質形態留傳下來,并向現代人展示的只有建筑時尚。俄國著名作家果戈里曾經說過:“建筑同時還是世界年鑒,當歌曲和傳說都已緘默時,只有建筑還在說話。”
城市文化內含四個層次:(一)物質秩序或物質文化層,即城市的建筑文化,包括城市建筑風格、特色與色彩的文化內涵,街區的結構與風貌,城市的建筑布局等,它們構成的居住結構;(二)管理--制度文化層,包括城市管理的體系、社會分層、社會組織等,它們是人--都市的社會結構;(三)生活與行為的方式層,即都市的活力,包括城市居民的生活習俗,日常交往方式,國際化全球隊化的的程度、時尚等;(四)心理--觀念文化層,即意識形態,如宗教觀念、政治觀念、道德情操、哲學理念、藝術底蘊及其所屬的機構,如學校、圖書館、博物館、劇院、書店和網吧等,是一種“精神文明”的秩序,人文價值觀念層次。四個層面文化的靈魂和核心是人文價值,整個城市文化不過是由這一核心而外化構成的文化價值體系。文化是城市的靈魂,是時尚的符號,是族性與歷史的敘述,是城市人格價值的訴求。
一個富有歷史內涵的城市,其街區的建筑物是源于不同歷史階段的空間交叉連接,它們是作為“意義族群”在默默地相互對話,呈現互文性。體現多層性和多元性。建筑風格是一種獨特的時尚,她記錄著歷史,表現著文化的追求。在你面對這些建筑時會不由的思考歷史瞬間所可能容納的生活交往的歷史事件、歷史場景,借以尋找其意義。當你站在北京故宮內的青石階上,登臨萬里長城的烽火臺,站在古鎮周莊的雙橋上,站在南京中山陵前,站在鎮江金山古寺前聆聽古剎鐘聲,站在樂山大佛前仰視大佛,在埃及的金字塔前,在雅典衛城和帕特農神廟前,登上法國的埃菲爾鐵塔,在德國科隆大教堂內抬頭凝望深邃的穹頂,飛臨美國自由女神像而俯身觀望,乘游輪觀賞澳大利亞悉尼歌劇院,站在澳門那鑲嵌著大海藍色波紋的市政中心廣場上,環顧四周鱗次櫛比的歷史的與現代的,歐洲的與中國古代的歷史建筑,是否會引起你強烈的歷史感和懷舊情緒,或感受到佛祖、宙斯神、上帝的神秘莫測,或感覺到人的偉大與渺小,或充滿對自由的神往……。世界上眾多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國家,風格各異的歷史、社會、文化與族性,無一例外地都選擇了差異的建筑來作為其意義的存在方式。建筑風格或建筑語言,體現著它或它們各自不同的歷史、社會、族性、文化與國際化。
對美的城市來說,建筑群落是凝聚著詩性氣質的交往空間。巴斯德說過“文化是人們交流情感的方式”。德國當代社會學家哈貝馬斯也認為:交往是一種對意義的理解性活動,其目的在于達到共識。交往的本性尤其體現在建筑群落中。人類是合群交往的動物,他們的存在方式,如海德格爾所言,是一種共在,即“共同存在”。無論你在街頭逛商場購物,還是居家看電視、網上漫游,或者參觀博物館、美術館,或者到電影院看電影、到劇場看戲劇,或者步入舞廳、咖啡館、酒店、銀行、交易所、公園,甚至在市政會議大廳聽演講,都是一種社會交往,都要與他者相遇,因而都需要一種適合于你的交往空間,即建筑空間。然而,交往是一種文化方式,交往空間具有一定的文化特征。城市建筑是一個多元的文化劇場,是一個流動的、漂浮的而又保持對話的網絡體系,是一個具有多種解讀可能性的差異性文本。
內斯托·加西亞·坎克里尼在其《混合文化》一書中對城市、特別是具有悠久歷史的城市建筑文化的多元混合現象進行了深入的研究,認為:一個富有歷史內涵的城市,其街區的建筑物是源于不同歷史階段的空間交叉連接,它們是作為“意義族群”在默默地相互對話,呈現互文性。歷史建筑雖然凝聚著歷史文化的意蘊,但是其建筑話語和文本依然有待于今天的解讀。事實上,在現實中存在著兩種建筑傳統:活著的與死去的。建筑只有在使用中、在不斷納入當代人的生活交往中,才不斷發生新的、對建筑文本的閱讀與理解行為,也才能使古老的建筑潛在的特質與意義對當代人開放,在開放與閱讀中重建意義體系。而已經退出、不再進入閱讀性交往的建筑、其文化則陷入死亡困境。當然這需要進行不斷的認知,反復的論證,才能確認、確診該古老建筑到底是死還是活。任何輕率的、非理性的舉動都是一種破壞,甚至是一種犯罪,為歷史所不容。
城市建筑文化與服飾文化、飲食文化、汽車文化一樣,深受哲學與知識時尚的影響。有人說,哲學文本是觀念的建筑;建筑是實體的文本。事實確實如此,建筑的結構、材料、色彩等要素都在時代觀念的變化中相應地變幻,成為一種流動時尚的凝聚。建筑、服飾、飲食、等等文化,都是一種交往性很強的時尚語言,隨時隨地因"新潮"而變化。建筑在格調、形式、風格、裝飾色彩等方面時時刻刻都在提示人們:她最能夠體現一個城市的歷史、社會結構與文化品格,也是城市人交往空間特點的象征。多元的、多層次的、具有差異性的、體現不同時代“時尚”的城市建筑文化是一個城市的基本的、獨特的風景線。她不僅具有文物價值,更具有文化價值(認識到這一點尤為重要),不可再生,必須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妥善加以保護、保存,以便開發、利用,使之成為地方獨特的景觀和潛在的與顯現的旅游資源,進而成為一方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撐。
二、城市化發展趨勢對古老城市建筑文化的選擇
中國是一個傳統的農業國,工商業總體上的不發達,使得城市的發展和城市化程度一直不高。但隨著工業文明在古老中國的生根、開花、蓬勃發展,中國各地的城市化浪潮呈現出洶涌澎湃之勢,城市人口超高速增長。建國以來五十年時間,上海、重慶的人口已達千萬,成為世界超大型城市,而南京、北京、天津、蘇州、無錫、徐州等城市人口也成倍、成數倍增長,而深圳等新城市更是呈數十倍、上百倍增長。與此同時,一些集鎮,甚至鄉村的城市化趨勢日益加劇,人口超高速增長。當今社會隨著工商業的繁榮,城市文化已成為世界各國文化的無可置疑的中心文化或優勢文化,城市化趨勢銳不可擋,從1950-2000年,世界人口增加了140%,即從約25億人增至60億人,其中城市人口增至30多億。2000年,發達國家城市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超過80%,而發展中國家城市人口的比重也從1950年的17%上升到40%以上。世界總人口的一半將居住在城市,而另一半也必須以直接或間接的方式與城市保持密切的聯系。英國考文垂大學地理系主任戴維·克拉克預言說:“世界上一半人口進入城市用了八千年。現在的預言是,再過不到八十年,剩余的人也將完成這個過程。”
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劇,城市人口的飛速膨脹,古老的城市結構和城市系統難以承受日益增多的城市人口的重壓,交通和住房問題日益突出,狹小的街道、低矮的平房,阻礙了城市化進程,城市改造勢在必然。對此,各地所采取的手段和方式各不相同,主要有以下做法和傾向:一種是在舊城基礎上進行大規模的拆建,以拓寬道路,改建新式住宅。同時對成片的或者零星的具有歷史價值或文化意義的典型建筑予以妥善保護、修復或遷建,盡可能為我們所住的城市保存一絲文脈。這種方式在舊城歷史較短、古老建筑物不多和城市建筑缺乏特色的地區或地塊是可行的,如上海、深圳。但對舊城歷史悠久、歷史建筑集中和城市建筑文化特色顯明、具有文化(注意這里不僅僅是指文物)保護價值和旅游資源開發價值的城市,則不能采用,于是第二種模式隨之產生,即在盡可能地完好保持老城原貌的前提下,另辟地塊建設新城區,顯現城市文化中心與結構中心向邊緣化轉變的傾向。如潮州、蘇州、麗江、平遙、泉州等即是,并且不惜代價將原來建在老城區的工廠以及鋼混結構的建筑遷出老城區,遷出保護區。這與發達國家,在生態主義與環境保護觀念的催動下,“深藍運動”、“反城市化”或“消解城市中心”、“強調邊緣化”的后現代城市文明或后現代生存文化浪潮,雖有明顯區別,但城市中心居住區內森林化,大片綠蔭、鮮花與樹叢相映成輝,城市生態化、鄉村化趨勢有異曲同工之妙。
第三種傾向,即過分地、片面地強調發展,片面地強調改造舊城以改善原住民的居住條件(實際上原住民在新樓建成后,因房價高購買不起,不得不選擇較遠的城郊居住,舊城改造的最大受益者是開發商及少數以權謀私者),不顧歷史,不顧客觀實際,缺乏長遠打算,缺乏文化保護意識,不加區分地將舊城區、將老街夷為平地,或改造得面目全非。浙江的定海古城、天津的估衣街(尚剩半條街)、湖北的襄樊古城墻等文物、文化古跡就是如此。人類社會的發展歷史表明,經濟上處于弱勢的民族和國家,在文化上往往會自我輕賤,會盲目抄襲強勢國家的文化。可是,一旦喪失了自己的文化,那么,這個民族就會失去基本的信仰,從而面臨強大的精神危機,這要比物質貧困來得更為可怕。一個城市的建筑,不僅具有物質價值,還具有文化價值、精神價值,它是有性格、有精神、有生命的。對城市的傳統建筑文化,你若把它視為一種精神載體,你就會尊敬它、珍惜它、保護它;你若把它僅僅視為一種物質載體,你就會輕視它、漠視它,就會無節制地使用它,任意地改造它,隨心所欲地破壞它,甚至毫不憐惜地毀滅它。
事實上,西方發達國家的大中城市在舊城改造過程中,所拆毀的基本上是一些現代主義建筑風格的建筑。英國“后現代”建筑理論家查爾斯·詹克斯在其《后現代建筑語言》一書中幽默地宣告:“現代建筑于1972年7月15日下午3點32分在密蘇里州圣·路易斯城死去。”他所指認的是該城一大片50年代的現代建筑形式的住宅建筑用定向爆破作業方法被摧毀。代之而起的是一片后現代建筑,帶有回歸自然,具有仿古式傳統文化精神的建筑。現代主義建筑被稱之為“包豪斯(bauhaus)”建筑,它是20世紀50~70年代為適應資本在城市的擴張,需要大量廉價勞動力,而這些勞動力主體是工人,他們與傳統的豪宅大院無緣,迫切需要一種經濟實用的生存空間。作為一種現代城市的世俗精神的體現,包豪斯風格建筑的主要設計師格羅皮烏斯重視低收入家庭的住宅需要,突出經濟性,使這一風格將一切古典的繁文縟節的裝飾一筆勾銷,盡量采用簡潔實用的材料與造型。因此,大批灰色、造型簡單、造價低廉、強調平頂、大玻璃窗、追求陽臺、標準化、規則化、缺乏個性的普及型、“火柴盒”式的多層建筑拔地而起,成為中國城市的主體建筑和主要景觀,整個城市的傳統色調被淹沒在這一灰色之中。
這種“火柴盒”式的多層建筑經濟實用,體現了現代工業文明的精神,從平民百姓住宅的功能研究,進而影響到街道的設計,乃至整個城市甚至全國性的規劃。全國各地,從東部沿海到西部邊陲,從南疆到北國,從城市到鄉村,一種模式,一種風格的“新工房”遍地開花。現代主義文化大肆張揚人的主體性,弘揚人對自然的絕對統治權威,城市成為人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典范。城市,意味著人對自然狀態的不滿和忤逆,意味著人與自然關系的疏離,由此造成人與自然、城市與鄉村、社會與自然、人類與其它生命之間的二元分裂和對立。城市建設中“圈地運動”的迅猛比以往任何時候都來得可怕,簡易工房和包豪斯風格建筑所構成的城市“水泥森林”取代自然植被而裹挾著人們。由于過分強調居住而忽視休閑與消費,致使城市街道狹窄,樓宇間距離較近,缺少城市公共綠地,人口過量,城市擁擠不堪,工業煙塵遮天蔽日,城市垃圾堆積如山,污水橫流,環境污染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都市生活緊張繁忙,工作重復單調,制度等級森嚴,生活空間局促狹小,居民生活單調、枯燥、無聊,人居環境因遠離自然而惡化。現代工業文明在造就了巨大成就的同時造就了普遍的異化現象,科學與理性不再天然與人內在相伴,而是變成了異己的力量。現代工業文明滋生的弊端,促使20世紀后期的人們不斷的反思:如何構建科學合理的城市建筑文化理念?
三、城市建筑文化的爭辯與后現代建筑文化理念
二十世紀,都市文化學的一個重要主題,即文化激進主義與文化保守主義的激烈爭鋒。這一爭論的焦點,即表現在現代主義與后現代主義對傳統文化的看法上大相徑庭。文化激進主義曾經是走向現代化城市文明的推進者,他們否定與遺棄傳統文明,強調創新與變革成為現代文明的生存價值。在中國城市的精英文化層面,“五四”時期,中國的一代文化精英,如胡適、錢玄同、魯迅等對傳統,特別是對孔孟儒學持激烈的批判態度。將作為人文精神象征的儒學與科學精神兩者對立起來,加之儒學的封建傳統意義,按照其“順昌逆亡”的進化論邏輯,就很難不被“打倒”和“橫掃”,憤世嫉俗的“五四青年”作民族的自我批判、自我革命、自我否定,在當時特定條件下,是必要的,起到了振聾發聵的作用,具有重大的現代意義。
但是,“五四”新文化運動所倡導的科學精神是單一主體性的,采取的方式是消解而非認同,他在對待自然與他者關系問題上具有明顯的獨斷霸權風格,缺乏深厚的人文精神,未能體現多元現代性。從總體上說,現代主義與傳統主義的二元對立和相互排斥,乃至激烈斗爭,是20世紀初中期中國文化的主要景觀。從“打倒孔家店”、搗毀孔廟;從“盡數封閉中國戲館”,甚至要“廢滅漢字”,“不要讀中國書”,到“”的火紅歲月,在那“破舊立新”的現代主義沖動下,無數的都市古老建筑、舊物在一夜之間被拆毀、砸碎了:老房子、老城門、老城墻、老胡同、老街道、老橋、老字號店鋪及老家具、老古董等,多少傳統在這一沖動中銷聲匿跡!而史無前例的“”,實際上是革了文化的命,又有多少城市的文物、文化古跡慘遭浩劫而蕩然無存!多少古籍經典甚至字畫、瓷器等也被套上“四舊的帽子”而橫遭毀滅!
隨著改革開放步伐的加快,城市義不容辭地成為工業化的中心。勢不可擋的城市化進程,致使許多城市的領導人和管理者,狹隘地、片面地理解“發展”、“開發”,片面強調城市功能,將城市改造和房地產開發對經濟的拉動、居民居住條件的改善對立起來,在所謂“合理”、“合法”的旗號下,作出了非理性的沖動的舉動,不分青紅皂白地將慘遭浩劫而殘存下的為數不多的體現城市歷史及其文明發展軌跡的古老建筑,毀滅殆盡!取而代之的是現代主義的普遍理性模式———存在的只是毫無個性的城市,同步化、模件化、工具化、標準化的人居場所和城市景觀,乃至社區文化和公眾生活。托夫勒所總結、歸納的工業文明時期的現代主義城市文化的六大規則———標準化、專業化、同步化、集中化、好大狂、集權化,在中國的大地上也得到了充分的體現。
一樣的包豪斯建筑群,一樣的高樓大廈、一樣的水泥柏油馬路、一樣的商場、一樣的車站、一樣的電線桿、一樣的汽車、一樣的自行車;抽象的雕塑、馬賽克貼面磚、灰色的水泥墻、刺眼的玻璃幕墻,到處都雷同;甚至在大家剛剛脫下一樣的灰藍服裝之后,立刻又穿上了一樣的西裝、一樣的工作服;一樣的標準化的家庭裝飾;千萬人看同一電視節目,聽同一廣播新聞,讀同一種報紙;接受標準化的教育,一樣的教科書,一樣的考試題,一樣的標準答案,……,不一而足。工業化城市到處都“家族相似”,成為一個類型,似乎是被“克隆”出來一樣,萬城一面,特色全無。城市失去了往日的傳統文化的標識,一些古典建筑的殘垣斷壁,在高樓大廈身后成為一個破舊不堪的淡淡的影子,有些城市甚至連這點淡淡的影子也消失得無影無蹤,活脫脫一個沒有發展歷史的新興水泥城堡。
直到二十世紀末,隨著中國的改革與開放的深入,經濟的飛速發展與繁榮,后工業文明時代悄然來臨,文化領域也迎來了后現代主義。根據文化學家伊布爾·哈桑的研究,后現代城市文明或后現代生存文化也具有六大基本特征———多元差異性;消解中心性,強調邊緣化;反整體性和宏大敘事,強調斷裂欲差異;反對基礎主義和深度模式,強調平面化;反對意義的先驗控制,主張能指鏈的膨脹、撒播與斷裂;生態倫理與可持續發展觀。后現代主義是對現代主義的反叛,后現代主義力求“返本開新”,文化保守主義成為一種新的城市時尚。從某種意義上說,后現代文明是建立在重新解讀城市歷史傳統的基礎上發生與發展起來的。古老的建筑語言,封存已久的傳統精神正在被“啟封”,重現魅力;被現代主義否定的城市傳統文本正在被重新解讀;回歸傳統,返本開新正在成為一種新的城市文明創新的某種形式。
歷史、傳統、陳跡、文本,所有在現代主義視野中毫無價值、應被否定拋棄的東西,都在后現代地平線上閃耀著新的世紀之光。“回到傳統去!”的欲求使得傳統地位飛速飆升,恰似經歷漫長歲月的冬眠之后忽然如沐春風。二元對立消解了,“復制傳統”成為后現代的首要任務。正如美國學者大衛·格里芬所言,當跨過激烈的反傳統的現代主義階段之后,后現代主義向傳統主義頻送秋波,“仿佛向舊事物的回復”,以期“返本開新”。后現代主義在解構現代主義的基礎上,通過對文化傳統的“再認識”,或重新認識而開拓創新的。歷史的文化,在當代重新顯現魅力。老房子、老城門、老城墻、老胡同、老街道、老橋、老字號店鋪、老牌坊、老村莊、老城鎮、老廟及老家具、老古董、老照片乃至老式的服裝,……等等。凡是老的、舊的,具有差異性、地域性、族性特色的文化存在物,作為反叛現代主義的文化資源,與后現代主結成聯盟,在城市文化中大肆流行。秦磚漢瓦、唐宋城墻、明清民居,在街區空間對話中保持著巨大的張力。北京的四合院、胡同,泉州的古城,蘇州的觀前街,南京的夫子廟與明城墻,上海的城隍廟、里弄、老街、石庫門建筑、外灘和茂名路的近代建筑、江灣三十年代的市政中心、衡山路和山陰路的名人故居與花園住宅,天津的宮前街、估衣街等等,各地保留下來的古典建筑與周圍民居渾然一體,相得益彰。而越是古典的,就越有文化魅力,也越有久遠的歷史前景和文化旅游資源的開發價值。一些有名的或從未聽說過的古城、古鎮乃至鄉野古村落的歷史建筑紛紛被“發現”、被“挖掘”出來,“重見天日”,成為旅游勝地,乃至一舉成為世界文化遺產而蜚聲中外。如蘇州的周莊、同里古鎮,云南的麗江古城(世界文化遺產),安徽的西遞、宏村古村落(世界文化遺產),山西的平遙古城(世界文化遺產),江西撫州的流坑村(被譽為千古第一村),浙江的南溪江古村落和西塘古鎮等等。
與此同時,后現代主義還使人們終于跨越了與自然為敵的階段,走向崇尚返璞歸真,強調人與自然和諧統一的后現代之旅。人們與大自然,特別是綠色植物的親和力與日俱增,處處尋找那失落的自然之友。久違的綠色又在后現代觀念催化下回到了城市生活。大塊的城市公共綠地,成片的城市森林,清澈的湖水,鮮艷奪目的花叢,使人居環境日益顯得綠色蔥蘢,充滿了生命的活力。新加坡在這方面是一個杰出的典范。廣東的珠海也是一個成功的范例,被聯合國評為最佳人居城市之一。上海浦東陸家嘴金融區的大片綠地,徐家匯商業區的工廠在搬遷后,建成格調清新別致的徐家匯公園,城市規劃和城市建設體現了遠見與大手筆。
后工業文明對城市建筑的滲透,隨著城市的改造和城市的發展來到我們的身邊。后現代主義建筑風格主要體現在對歷史古典傳統的某種模仿與回復。后現代在都市建筑中力求復制傳統,它在現代金屬廊柱的頂端加上一個古典式的蓮花包頭,或在高層建筑的平頂上加上一頂民族化的頂蓋,或將一座完全現代意義的民居包上完全民族化的外表,以實現所謂“中體西用”,或者干脆按照歷史記錄來重建古典名園,使毀于歷史的著名建筑重見天日。于是,大屋頂樓房、雕梁畫棟的牌樓與建筑在絕跡多年以后又在中國的許多城市、甚至在其他各國的唐人街上悄然興起。如杭州的宋城、無錫的三國城和水滸城、揚州的唐城、徐州的漢城、西安的唐城、上海的城隍廟等等,全國各地的仿古街更是一涌而上。許多地方是一面拆毀老街,同時又在投資加緊建設新的“老街”,真是一幅荒唐、滑稽,叫人欲哭無淚、欲笑不能的諷刺畫。
與此同時,西方的、歐洲的、印度的、南美的、泰國的等等其他民族和國家不同文化背景和不同建筑風格的傳統建筑,也在中國的許多城市生根、開花,如無錫的歐洲城、上海和北京的世界城;而中國的古典名園也被世界其他國家移植、復制,如蘇州園林被復制到美國紐約的現代化建筑群中。一切具有古老文化傳統和差異特色的建筑樣式,都煥發出了新的生命與活力,一切具有古老文化傳統的城市都在各自的現代性建筑中揉進了古典主義的裝飾,從而讓不同的文化精神與語言在城市的某一座建筑上展開對話。后現代就是這樣與傳統文化在建筑語言的對話中達到視野的融合。深厚的傳統文化底蘊,將城市建筑文化景觀出色地表現出來,成為一種后現代所崇尚、欣賞的差異性,成為與中國乃至全球其他城市進行對話的文本,成為一種向世界開放交往的形式載體。
當然,后現代重視傳統、借助傳統、復制傳統只是為了超越現代主義,而不是簡單的回歸傳統和全面復古。古典建筑、古典音樂舞蹈、古典服飾、古代經典、古典器具等等,都在當代人的精神結構中被漸漸地認同、融化。重新解釋不僅意味著文化的遺傳,更意味著創造,而創造的基本形式在于構建新的文化對話的交往結構。一切文化,尤其是建筑文化,其存在的價值和生命存在方式就是交往。只有不斷的交往,不斷地將建筑的文化信息向外傳播,建筑文化的傳統才能不斷地被激活,才能在被激活的過程中不斷地參與構建新的文化體系,不斷地下傳遺傳因子,從而使傳統建筑文在不斷地遺傳過程中獲得永生。